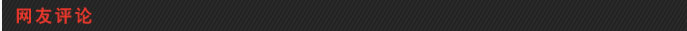胡新民:梁漱溟和毛澤東爭辯的真相
梁漱溟是我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會(huì)活動(dòng)家。甲午戰(zhàn)爭前一年出生的他,與同時(shí)代的志士仁人一樣,為民族獨(dú)立、為國家富強(qiáng)積極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實(shí)現(xiàn),先贊成“君主立憲”,后來轉(zhuǎn)入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shè)新中國的“路向”。他認(rèn)為實(shí)現(xiàn)強(qiáng)國之夢必須從鄉(xiāng)村入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huì),并積極從事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實(shí)踐。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第一至四屆政協(xié)委員,第五屆和第六屆政協(xié)常委。中國農(nóng)村問題始終是他最為關(guān)注的問題之一。
梁漱溟的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1953年9月與毛澤東的公開爭辯。這件事情當(dāng)時(shí)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直到“文革”結(jié)束后才算是廣為人知。一時(shí)間,諸如“犯顏直諫”“廷爭面折”“為農(nóng)夫代言”“不為強(qiáng)暴所屈”等等贊揚(yáng)梁漱溟敢于犯上的錚錚風(fēng)骨的輿論沸沸揚(yáng)揚(yáng)。實(shí)際上這些看法都是相當(dāng)片面的。遺憾的是,至今仍有一些人步其后塵,發(fā)表類似不負(fù)責(zé)任的言論和文章。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歷史的真相,而且也可以說是對(duì)梁漱溟先生本人的不尊。下面就來還原一下這件事的歷史本來面目。
梁漱溟不顧一切要證明自己“熱烈擁護(hù)總路線”
新中國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極大地激發(fā)了全國人民的建設(shè)國家的熱情。全國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1952年底已經(jīng)達(dá)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同時(shí),抗美援朝也告訴中國必須走富國強(qiáng)兵之路。黨中央不失時(shí)機(jī)地提出了過渡時(shí)期的總路線,即“黨在這個(gè)過渡時(shí)期的總路線和總?cè)蝿?wù),是要在一個(gè)當(dāng)長的時(shí)期內(nèi),基本上實(shí)現(xiàn)國家工業(yè)化和對(duì)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huì)主義改造。”(毛澤東語)
后來廣為人知的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當(dāng)面激烈爭辯,就發(fā)生在一次討論總路線的會(huì)議上。這件事的全部經(jīng)過發(fā)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開始是全國政協(xié)常委擴(kuò)大會(huì)議,后轉(zhuǎn)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擴(kuò)大會(huì)議。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9月8日,周恩來給會(huì)議作了關(guān)于總路線的報(bào)告。9月9日,梁漱溟在小組討論中發(fā)言,表示贊同周恩來的講話,并對(duì)如何貫徹好總路線提了幾點(diǎn)建議。9月11日梁漱溟再次發(fā)言,話題仍然是如何貫徹好總路線,談到了三點(diǎn),最后一點(diǎn)是農(nóng)民問題,他說:“有人說,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農(nóng)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等等。9月12日毛澤東不點(diǎn)名地批評(píng)了梁的發(fā)言,認(rèn)為梁漱溟不同意總路線,拿農(nóng)民問題說事。梁感到受到莫大的冤屈,當(dāng)晚在氣頭上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表明他是擁護(hù)總路線的,希望有機(jī)會(huì)重復(fù)一次他的發(fā)言,以便了解他的“善意”。9月13日上午梁將信交給了毛,兩人在晚上談了約二十分鐘的話,毛仍認(rèn)為梁是反對(duì)總路線的,于是兩人“言語間頻頻沖突”。梁漱溟繼續(xù)向毛澤東要求安排他發(fā)言。于是,9月16日他在大會(huì)上發(fā)了言,重復(fù)了他在9月9日和9月11日的發(fā)言,“再三陳述自己并不反對(duì)總路線,而是熱烈擁護(hù)總路線的。”(見《梁漱溟問答錄》當(dāng)代中國出版社2013第114頁,此書經(jīng)梁漱溟親自審定----筆者注)
9月17日,周恩來作了長篇發(fā)言,第一次點(diǎn)了梁的名字,中心內(nèi)容是聯(lián)系歷史上的一些事實(shí),說梁是一貫反動(dòng)的。其間毛澤東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話,認(rèn)為梁漱溟是反對(duì)總路線的。梁漱溟更感到了莫大的冤屈,決定要繼續(xù)為自己辯護(hù)。9月18日開會(huì),梁漱溟上臺(tái)發(fā)言。他決定從歷史說起,必須要有“充分說話的時(shí)間”。于是,他要求毛澤東給他“雅量”。結(jié)果兩人又起沖突。這時(shí),臺(tái)下許多人反對(duì)梁漱溟的作法,要他下臺(tái)。
“毛澤東沒有叫我下臺(tái)。他口氣緩和地說:‘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講長了,把要點(diǎn)講一講好不好?’我說:‘我剛才講過了,希望主席給我充分時(shí)間。’毛主席又說:‘你講到四點(diǎn)鐘好不好?’我一看表都三點(diǎn)過了好多了,便說:‘我有很多事實(shí)要講,讓我講到四點(diǎn)哪能成!’”結(jié)果會(huì)場大嘩,幾個(gè)與會(huì)的人上臺(tái)發(fā)言批評(píng)梁漱溟。這時(shí),“毛主席對(duì)會(huì)場的人說:‘讓他再講十分鐘好不好?’”但是,梁漱溟不同意,仍然要求給他一個(gè)公平的待遇。接著會(huì)場又是大嘩,“毛主席又對(duì)我說,梁先生,再講十分鐘好不好?我依然回答:‘我有許多事實(shí)要講,十分鐘講不清楚。’”就這樣形成了僵局。最后有人提出請(qǐng)會(huì)議主席付諸表決,到會(huì)者大部分不贊成梁漱溟講下去,事情才結(jié)束。在表決前,毛澤東說會(huì)讓梁漱溟在另外一個(gè)會(huì)議上講。會(huì)議主席在表決后也告訴梁漱溟將有機(jī)會(huì)到另外的會(huì)議上充分地去講。梁漱溟后來是講了,但還是“沒有機(jī)會(huì)充分講自己的意見,主要是聽大家批判”。(引言均同上書第117頁、118頁)
事后,梁漱溟在至親好友的規(guī)勸幫助下,特別是在他的長子梁培寬的交心長談后,醒悟反悔。他認(rèn)識(shí)到自己的“倔強(qiáng)精神”和“骨氣”都是錯(cuò)誤的。他發(fā)現(xiàn)自己“敬愛包括毛主席在內(nèi)的許多一心為國家為民族的漢子,卻一直懷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動(dòng)路線”,以致造成了“9月18日達(dá)到頂峰的那場荒唐錯(cuò)誤”,因此“是必定要引起人們的公憤的。”同時(shí),也理解了毛澤東為什么說他是“以筆殺人”和“偽君子”。(引言均同上書第120頁至123頁)
基于這種認(rèn)識(shí),梁漱溟寫信給毛澤東,請(qǐng)求請(qǐng)長假閉門思過。此后,梁漱溟仍然擔(dān)任政協(xié)委員,參加國務(wù)活動(dòng)和外出視察,例如1954年初參加憲法草案修改討論等。但是,他再?zèng)]有機(jī)會(huì)與毛澤東當(dāng)面長談。只是在集體活動(dòng)中見到過毛澤東,在握手的時(shí)候寒暄幾句。
梁漱溟對(duì)自己的錯(cuò)誤做過多次檢討,他的態(tài)度完全是真誠的。這種態(tài)度一直延續(xù)到“文革”結(jié)束后。
從歷史背景來看梁漱溟的不足
在這個(gè)事件中,最不能使梁漱溟接受的還是周恩來說他一直想升官發(fā)財(cái),因?yàn)榱菏閺膩聿辉敢庾龉佟S幸馑嫉氖牵菏閷?duì)周恩來的最后的評(píng)價(jià)卻是一個(gè)“完人”。因此,對(duì)于這場爭辯,一定要結(jié)合當(dāng)時(shí)的歷史背景,才能作出比較切合實(shí)際的評(píng)價(jià)。關(guān)于這點(diǎn),胡耀邦的說法對(duì)我們正確認(rèn)識(shí)和理解這段歷史是很有幫助的。1985年5月10日下午,時(shí)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會(huì)見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紐約《華語快報(bào)》發(fā)行人陸鏗,雙方進(jìn)行了坦率的交談。談話中涉及到了梁漱溟和毛澤東的爭辯,現(xiàn)摘錄如下:
“胡耀邦:梁漱溟先生呢,從參加新中國的政治舞臺(tái)頭一天起,是不大講我們的好話的。他有他的想法,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這不要緊嘛……!
陸鏗:但是他老近來也講你們的好話了。
胡:他幾年之前就開始講我們的好話了,大概是四年以前吧,我記不很準(zhǔn)。
陸:當(dāng)然,這也是隨著形勢發(fā)展所起的客觀變化。
胡:盡管他不講我們的好話,也應(yīng)該允許人家嘛。在有些事上,還未經(jīng)過自己的腦子證實(shí),他一時(shí)有些想不通,從而不大贊成。后來就把他給批了一下。談起豁達(dá)大度,我們的毛主席是第一位的,后來……
陸:后來就變樣了……
胡:可能我們的毛主席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國家事情這么復(fù)雜,你卻那么樣的瞎放炮,不大好吧!那一年大概是五五年吧,就給批了一下,現(xiàn)在看是批過頭了。”
這里有兩點(diǎn)要注意:一是胡耀邦說毛澤東的豁達(dá)是第一位的。當(dāng)初梁漱溟9月8日第一次談到“九天九地”時(shí),周恩來作了解釋。后來毛澤東也批評(píng)了梁漱溟。但是,到了9月16日,梁漱溟又把“九天九地”拿出來說事。在9月18日,還要會(huì)議給他認(rèn)為足夠長的的時(shí)間來作解釋,這在全國性的會(huì)議上顯然是做不到的,這也是毛澤東的“雅量”所接受不了的。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提出在以后的會(huì)上安排他作解釋發(fā)言。這應(yīng)該就是胡耀邦所指的夠豁達(dá)。二是1955年的批判是針對(duì)梁漱溟的“唯心論”的,與農(nóng)民問題無關(guān),也就扯不到“為農(nóng)夫代言”而受到批判的事情。與此相關(guān)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那時(shí)批判梁漱溟的有一位中共著名的哲學(xué)家艾思奇,但若干年后梁漱溟認(rèn)真學(xué)習(xí)了艾思奇的哲學(xué)著作,并寫出了筆記。
對(duì)梁漱溟頗有研究的汪東林先生,即“文革”后最早在報(bào)紙上披露梁漱溟1953年事件的作者,在2006年對(duì)這件事的看法給出了這樣的背景解讀:這場沖突“應(yīng)當(dāng)說這里邊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諸如,根據(jù)當(dāng)時(shí)的國內(nèi)外環(huán)境和條件,中國要強(qiáng)兵富國,必須集中一切人力、財(cái)力發(fā)展重工業(yè),首先要顧及的是工業(yè)建設(shè)(含城市建設(shè))和工人利益,而實(shí)際上不可能也無力量顧及人口如此眾多、地域如此遼闊的農(nóng)民和農(nóng)村。又比如,為了集中一切力量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就必須統(tǒng)一思想,步調(diào)一致,突出政權(quán)穩(wěn)固和領(lǐng)導(dǎo)權(quán)問題,因而不允許梁漱溟發(fā)表這種有可能扭偏國家工業(yè)化大方向的‘錯(cuò)誤’意見,等等。”
應(yīng)該說,凡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形勢有所了解的人,基本上都會(huì)同意胡耀邦和汪東林的看法。梁漱溟的長子梁培寬也是這樣認(rèn)為的。1953年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兩個(gè)兒子培寬、培恕先后返家,梁漱溟便將前幾天所發(fā)生的意外風(fēng)波從頭至尾告訴他們,并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毛澤東完全是出于誤會(huì)。梁漱溟說完后,大兒子梁培寬即父親談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不要以為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發(fā)生,雖然看上去有許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中共負(fù)責(zé)人只是對(duì)你梁漱溟個(gè)人過不去。偶然因素與個(gè)人因素在這里都不居于主要地位。梁培寬特地分析道:毛澤東“并不是他個(gè)人對(duì)你個(gè)人有什么惡感或好感。毛澤東一切為了當(dāng)前國家的大業(yè),而沒有其他。因此,你考慮自己的問題時(shí),亦不要把它同國家當(dāng)前建設(shè)事業(yè)分開”(同上書第121頁)。
胡耀邦、汪東林和梁培寬等人的分析有助于我們比較全面了解事情的經(jīng)過。梁漱溟的思想很快發(fā)生了變化,是與他接受別人的勸導(dǎo)分不開的。他在與兩個(gè)兒子談話后認(rèn)為:“寬兒(指他的長子梁培寬)的這席談話,加上好友、學(xué)生的寬勸賜教,包括何香凝先生在會(huì)上對(duì)我的批評(píng)等等,引起我思路上心情上根本變化,對(duì)于自己錯(cuò)誤之所由似乎頓時(shí)有所發(fā)覺,好像通了竅。”另一個(gè)促使他思想變化的因素是他意識(shí)到他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農(nóng)村的情況了解得并不全面,心里并沒有底。這個(gè)“九天九地”的說法實(shí)際上是聽了他的老朋友彭一湖說的。因此,他懊悔了自己“不該將從朋友處聽來的話拿到大會(huì)上講”(見《梁漱溟先生紀(jì)念文集》第6頁中國工人出版社)。順便提一下,當(dāng)時(shí)梁漱溟發(fā)言完畢后,與會(huì)的周恩來就作出了解釋,用數(shù)據(jù)說明了城鄉(xiāng)差別并沒有那么嚴(yán)重。當(dāng)時(shí)的情況也的確如此。如果用系數(shù)比較,當(dāng)時(shí)的鄉(xiāng)村和城市的差別大約是1比1.5,而現(xiàn)在達(dá)到了1:比3.0以上!據(jù)中國社科院2013年12月26日發(fā)布的《社會(huì)藍(lán)皮書》披露,一般來講,發(fā)達(dá)國家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在1.5倍左右,發(fā)展中國家略高一些,為2倍左右,該倍數(shù)為基本平衡的程度。超過3倍以上,則說明收入差距過大,結(jié)構(gòu)失衡。由此可以看出,1953年的城鄉(xiāng)收入的差距是很正常的。
梁漱溟對(duì)毛澤東時(shí)代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贊不絕口
在促使梁漱溟思想變化的諸因素中,最重要的還是他自己的感性認(rèn)識(shí)的積累。他通過自己的觀察,包括親眼目睹的和從報(bào)刊雜志上看到的消息,再加上回顧了解放初期他在農(nóng)村看到的情況,終于認(rèn)定實(shí)際上當(dāng)時(shí)國家還是一直重視了農(nóng)業(yè)的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因而,他也就以積極的正面的眼光來看待那個(gè)時(shí)代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了。
梁漱溟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關(guān)心農(nóng)民問題的人之一。他早就認(rèn)為中國的出路在于搞好鄉(xiāng)村建設(shè),要切實(shí)解決好農(nóng)民問題。但是,舊中國的農(nóng)村情況是令他萬分失望的,他曾在1939年考察農(nóng)村時(shí)說道:“民國三十年來正經(jīng)事一件沒有做,今后非普遍從鄉(xiāng)村求進(jìn)步不可。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們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謂窮鄉(xiāng)僻壤,將民生之窮苦,風(fēng)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內(nèi)地婦女纏足,纏到幾乎不見有足,至須以爬行代步。還有黃河右岸窮谷中,婦女束發(fā)青衣白裙的裝飾,與京戲上所見正同,大約仍是明代的舊樣子。說到窮苦,更不勝說。普遍都是營養(yǎng)不足,饑餓狀態(tài)。其不潔不衛(wèi)生,則又隨窮苦及無知識(shí)而來。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社會(huì),縱無暴政侵略,亦無法自存于現(xiàn)代。故如何急求社會(huì)進(jìn)步,為中國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國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沒有做。一年復(fù)一年,其窮如故,甚陋如故。”(見梁漱溟《我生有崖愿無盡》)
新中國成立后,親眼目睹了兩個(gè)社會(huì)農(nóng)村的明顯不同,梁漱溟很快就感覺到了國家的變化、農(nóng)村的變化。這些都是他通過自己的觀察認(rèn)識(shí)到的。1950年4月初,他赴外地參觀訪問,在山東期間說道:“目睹工農(nóng)干勁十足,令人感奮。”(見李淵庭、閻秉華編著,梁漱溟親修的《梁漱溟》第219頁群言出版社)“在參觀了各地農(nóng)業(yè)合作社之后,先生(指梁漱溟)也認(rèn)為只要把分配問題解決好,認(rèn)真執(zhí)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政策,調(diào)動(dòng)農(nóng)民生產(chǎn)的積極性,那么,循由合作化道路可以逐漸走上社會(huì)主義道路的。”(同前書第220頁)1953年9月以后,梁漱溟保留了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身份,他通過參政議政,參觀訪問,對(duì)國家面貌發(fā)展變化,局面的穩(wěn)定統(tǒng)一,新事物的不斷涌現(xiàn),甚感欣慰。他相信了自己的“眼見為實(shí)”,因此在他的言論中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九天九地”之類的說法。盡管1953年后還是受到了多次批判,但心情隨著國家的日趨強(qiáng)盛而爽亮開朗起來,1953年的那件事所受的委屈也就漸漸淡漠。1956年他參加政協(xié)視察團(tuán)到甘肅視察了五十天,在談到農(nóng)業(yè)的時(shí)候說:“農(nóng)業(yè)方面呢,進(jìn)展的好象太猛,然而至少基本上是健康的。”(同前書第241頁)。他在參觀梅山水庫時(shí)在日記中寫道:“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產(chǎn)黨多矣!”他特別為中共八屆八中全會(huì)決議而高興。因?yàn)闆Q議說大規(guī)模的階級(jí)斗爭已經(jīng)過去,全國人民都應(yīng)該團(tuán)結(jié)起來向自然開戰(zhàn)。他認(rèn)為人民公社、“土洋結(jié)合”、大躍進(jìn)等等,都最能發(fā)動(dòng)群眾,調(diào)動(dòng)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梁還寫出了《人類創(chuàng)造力的大發(fā)揮大表現(xiàn)---建國十年一切建設(shè)突飛猛進(jìn)的由來》,不吝筆墨地稱贊毛澤東的領(lǐng)導(dǎo)才能。梁培恕后來回憶道“父親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寫書肯定‘大躍進(jìn)’的人。”
客觀而論,梁漱溟在1950-1960年代對(duì)農(nóng)村的看法有所偏頗,不夠深透,而且輕信了當(dāng)時(shí)的報(bào)刊雜志上的消息。但是,不容否定的是,梁漱溟對(duì)新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對(duì)共產(chǎn)黨的擁護(hù)、對(duì)毛澤東的欽佩確實(shí)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1960年9月,即1953年的事件過去了七年之后,梁培恕生了一個(gè)兒子,梁漱溟親自為其嫡孫取名欽東。寓意“欽佩毛澤東”。1961年,他寫道:“很久走著下坡路的中國人,自從全國解放后扭轉(zhuǎn)過來走著上坡路”“領(lǐng)導(dǎo)何以這樣得法而竟收功若此”(見李淵庭、閻秉華編著,梁漱溟親修的《梁漱溟》第248頁)。梁在出席1964-1965的全國政協(xié)四屆一次會(huì)議和列席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huì)議時(shí),作了長篇發(fā)言表明了他的心跡:
“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人民群眾的精神力量從來沒有像新中國成立以后這樣得到大發(fā)揮、大表現(xiàn)。顯然六七億人如果沒有共產(chǎn)黨毛主席,恐怕今天也還是一盤散沙、癱瘓無力的,出現(xiàn)不了什么奇跡。為什么共產(chǎn)黨毛主席能領(lǐng)導(dǎo),而旁人不行?”
經(jīng)歷了“文革”以后,梁漱溟在不同的場合仍基本上還是堅(jiān)持了他的這個(gè)看法。在1978年的政協(xié)會(huì)上他說道:“我國過去的成功和勝利,的確是靠毛主席的領(lǐng)導(dǎo)”。他還一再強(qiáng)調(diào):“我并不因?yàn)檎f他,批評(píng)他,而否認(rèn)他的成功”,“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二三十年來,中國國內(nèi)的建設(shè)、國外的威望,沒法不承認(rèn)是了不起的成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終生都把中國農(nóng)村問題作為自己研究重點(diǎn)的梁漱溟,他的不少看法對(duì)改革開放的今天仍有相當(dāng)重要的意義。
此文原載《黨史博采》2014年第五期,原標(biāo)題《梁漱溟和毛澤東公開爭辯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