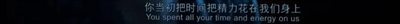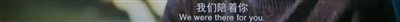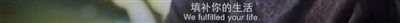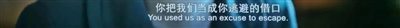電影《我本是高山》,我看了兩遍,產(chǎn)生了“兩個(gè)問(wèn)題”。
第一個(gè)問(wèn)題是,為什么張桂梅對(duì)師生這么“苛刻”,也就是說(shuō)她“苛刻”的合理性在哪里?
第二個(gè)問(wèn)題是,為什么張桂梅要選擇這項(xiàng)艱苦的事業(yè),也就是說(shuō)她的“動(dòng)力之源”在哪里?
把這“兩個(gè)問(wèn)題”闡釋清楚了,就可以算是一部好電影。但是,電影《我本是高山》,只解釋了第一個(gè)問(wèn)題,沒(méi)解釋甚至是扭曲了第二個(gè)問(wèn)題。
首先,我們探討第一個(gè)問(wèn)題——張桂梅為什么這么“苛刻”?
電影《我本是高山》,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張桂梅的一句話:“我不是在教書(shū),我是在救人!”
這群山里的娃娃,都是初中沒(méi)畢業(yè)就輟學(xué)的女孩子,她們?nèi)绻蛔x“女高”,不上大學(xué),最有可能的命運(yùn)就是留在大山里嫁人生娃,能走出去的,多是“打零工”——做餐飲服務(wù)員、家政清潔工、超市收銀員、工廠流水線等等。稍微有點(diǎn)姿色的,也極容易被這個(gè)“兩極分化”的叢林世界卷進(jìn)酒吧、夜店、會(huì)所、KTV、足浴店這些烏七八糟的場(chǎng)所,去從事什么DJ、美容、模特、技師、公主等灰色職業(yè)。(不是歧視從事這些職業(yè)的人,而是反對(duì)兩極分化下的職業(yè)壓迫。)
電影《我不是高山》雖然沒(méi)有這么赤裸裸的描述,但僅從學(xué)生“山英”在餐飲店門(mén)口傳銷式的亂喊亂叫就可見(jiàn)一斑。
什么“今天加油一百萬(wàn),明天加油五百萬(wàn),天天加油一千萬(wàn)”,這種洗腦式的喊叫和張桂梅讓學(xué)生朗誦“我生來(lái)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于群峰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我生來(lái)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二者形成多么鮮明的對(duì)比!
前者是洗腦,后者是覺(jué)醒;前者是壓迫,后者是救人。這種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感,就是在告訴觀眾——張桂梅的“教書(shū)”,本質(zhì)就是在“救人”,就是在幫助山里的女娃娃逆天改命,讓她們有擺脫大山的自由,有拒絕某些職業(yè)的自由,可以自由地選擇去當(dāng)醫(yī)生、當(dāng)律師、當(dāng)記者、當(dāng)護(hù)士、當(dāng)戰(zhàn)士,以避免掉進(jìn)社會(huì)欲望的陷阱而蹉跎青春。
理解了這一層,也就能理解了張桂梅看似不近人情的管理——她不讓學(xué)生們留長(zhǎng)發(fā)、不讓老師們休假、不讓女老師懷孕、每天凌晨五點(diǎn)多就用小喇叭“吼”學(xué)生們起床······
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救人”的基礎(chǔ)上的。相比于困溺于大山叢林,深陷于血汗工廠,混沌于酒吧夜店,掙扎于欲望旋渦,晚兩年生孩子,早兩個(gè)鐘頭起床,又算得了什么呢?
“父母之愛(ài)子,則為之計(jì)生遠(yuǎn)”。張桂梅看似不近人情,實(shí)則是把學(xué)生當(dāng)“人”看,她跋山涉水去家訪,拿自己工資給學(xué)生配助聽(tīng)器,在她嚴(yán)苛的背后,更有無(wú)微不至的關(guān)愛(ài),她希望孩子們不當(dāng)溪流、不做溝壑、不淪為草芥,而是堂堂正正地做人。反言之,讓學(xué)生隨波逐流,輟學(xué)回家,恰恰是對(duì)學(xué)生最大的不負(fù)責(zé),讓他們?cè)谏鐣?huì)上作為廉價(jià)勞動(dòng)力賣來(lái)賣去,難道這就是你所希望的“寬容”?難道不是殘忍嗎?
“徐影影”這樣的小資是很難解張桂梅的。我們應(yīng)該相信,就算死了張屠夫,也不會(huì)吃混毛豬。走了徐影影,留下了盧南山,新來(lái)了付春盈,女高的心更齊了,阻力更小了。
所以,第一個(gè)問(wèn)題,影片是做了比較好的闡述的。
接下來(lái),我們探討第二個(gè)問(wèn)題——張桂梅為什么要選擇這么艱苦的事業(yè),她的動(dòng)力之源到底是什么?
影片將張桂梅的事業(yè)選擇,簡(jiǎn)單地歸因成“填補(bǔ)了愛(ài)情的空虛”。我認(rèn)為這是不恰當(dāng)?shù)摹?/p>
徐影影不理解張桂梅為什么對(duì)師生那么苛刻,在這一點(diǎn)上,付春盈是理解并支持張桂梅的。但是,在第二個(gè)問(wèn)題上,付春盈出現(xiàn)了動(dòng)搖。電影通過(guò)付春盈之口,假想了張桂梅的內(nèi)心世界,認(rèn)為她是出于一種另類的“私心”,找山區(qū)學(xué)生完全是為了填補(bǔ)內(nèi)心的空虛。
很明顯,付春盈說(shuō)的是氣話,卻迎合了一些觀眾的胃口:人都是自私的,沒(méi)有所謂的崇高。但是,我認(rèn)為影片安排付春盈懟張桂梅的話語(yǔ)邏輯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張桂梅自己也承認(rèn),丈夫董玉漢的早逝,對(duì)她的打擊是巨大的,她傷心、難過(guò),甚至失魂落魄。這恰恰說(shuō)明,她是一個(gè)有血有肉的真實(shí)的人,而不是什么“道德機(jī)器”。問(wèn)題的關(guān)鍵是,這么大的打擊,為什么會(huì)讓她放棄城市的工作,選擇去山區(qū)長(zhǎng)期從事艱苦的教育事業(yè)?而不是其它?
要知道,90年代的中國(guó),到處充滿著商機(jī),到處彌漫著投機(jī)。她完全可以下海經(jīng)商,通過(guò)“發(fā)財(cái)”去彌補(bǔ)“愛(ài)情的空虛”啊;她也可以給學(xué)生有償補(bǔ)課,像有些老師一樣——“一個(gè)暑假一套房,一個(gè)寒假一臺(tái)車”——通過(guò)“買房購(gòu)車”去彌補(bǔ)這個(gè)空虛啊;她亦可以投身到職稱評(píng)定的名利場(chǎng)上,通過(guò)買論文、參加說(shuō)課比賽去評(píng)特級(jí)教師嘛;或者通過(guò)轉(zhuǎn)行政崗,千方百計(jì)當(dāng)官往上爬,牛逼轟轟地頤指氣使,這不也可以填補(bǔ)空虛么?
為什么張桂梅不去做這些,而選擇了走最難的山路、教最窮的娃娃,去搞山區(qū)教育事業(yè)呢?這個(gè)關(guān)鍵問(wèn)題,電影蹊蹺地避而不談。
要知道,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站在“人性”的制高點(diǎn)上質(zhì)疑“張桂梅是不是有神經(jīng)病?”,電影導(dǎo)演臆想通過(guò)“人性”回應(yīng)“人性”,大量展現(xiàn)夫妻溫存的畫(huà)面,試圖讓一些人去接受“小確幸”張桂梅,以抹掉她“神經(jīng)病”的標(biāo)簽。然而,這種避實(shí)就虛的表達(dá)方式,也許迎合了“小我”,卻矮化了真實(shí)的張桂梅同志。
大家都知道,宣傳作品,應(yīng)該是來(lái)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這部電影呢?是來(lái)源于生活,卻低于生活。因此,我認(rèn)為《我本是高山》是一部拍到“半山腰”的電影——它解釋了張桂梅“苛刻”的合理性,卻扭曲了張桂梅選擇這項(xiàng)崇高事業(yè)的動(dòng)力之源。
張桂梅,生于紅旗下,長(zhǎng)在新中國(guó),她毫不掩飾地說(shuō):“一直支撐我的是信念,是對(duì)黨的信仰。”這種信念實(shí)際來(lái)源于她對(duì)《紅巖》中英雄人物江姐的崇敬,這顆紅色的種子在她的孩童時(shí)期就已經(jīng)種下,在她40歲的時(shí)候破土而出。
1997年,也就是她丈夫去世后的第二年,張桂梅患病累倒在工作崗位上,她子宮內(nèi)的肌瘤有5個(gè)月胎兒那么大,需立即住院治療。可是當(dāng)初為了給丈夫治病,張桂梅已經(jīng)花光了兩人的積蓄。
就在她患難之時(shí),華坪人民通過(guò)捐款伸出了援助之手,安慰她:“你不要怕,我們?cè)俑F,也會(huì)救活你”,甚至有位婦女把僅有的5塊車費(fèi)捐出來(lái),自己走了6個(gè)多小時(shí)山路回家。
草木知春人念恩。張桂梅面對(duì)這樣的人民怎能不感動(dòng)?張桂梅哽咽著說(shuō):“我沒(méi)為這個(gè)小縣做過(guò)一點(diǎn)點(diǎn)貢獻(xiàn),卻添了這么大的麻煩。他們把我救活了,我活著要為他們干些什么。”
人活著為了什么?怎么活?這個(gè)重大的人生觀問(wèn)題,張桂梅從生命的逆境中找到了答案。
她在華坪縣一方面感受到了組織的溫暖,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學(xué)生們艱辛:有學(xué)生冬天穿著一兩塊錢(qián)的塑料涼鞋;有學(xué)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jìn)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甚至還有學(xué)生是孤兒,無(wú)依無(wú)靠······于是,她常帶學(xué)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xué)費(fèi)、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
張桂梅開(kāi)始反觀自己:“我不缺吃,不少穿啊,天災(zāi)人禍自己應(yīng)該明白。”她不再糾結(jié)于個(gè)人情感,把心思轉(zhuǎn)移到了學(xué)生們身上,辦起了華坪縣女子高中,走出了“小我”,成就了“大我”。
1998年4月,張桂梅光榮地加入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那年她41歲,比很多人入黨晚。但不同的是,她是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也入了黨。
張桂梅的信仰是很明確的,她辦學(xué)的邏輯是很清楚的,可是電影偏偏要用那種“夫妻之情”來(lái)替換張桂梅同志的“紅色種子”,這樣的手法太拙劣,太低級(jí),也太小瞧觀眾的審美水平和政治覺(jué)悟。
那一年,在入黨申請(qǐng)書(shū)上,她寫(xiě)道:“我要做焦裕祿一樣的人……”
記者問(wèn),“一直撐著您的是什么?”
“是共產(chǎn)黨員的信仰,是我對(duì)黨的承諾”,張桂梅說(shuō),她要做的不僅是幫這些女孩子們走出大山,更是要把她們培養(yǎng)成社會(huì)主義接班人,“忠于黨,忠于人民,去做更大的事。”
這才應(yīng)該是整部電影最大的亮點(diǎn),最值得書(shū)寫(xiě)的地方。
謹(jǐn)以此文,致敬“七一勛章”獲得者、中共二十大代表、全國(guó)婦聯(lián)副主席、麗江華坪女子高級(jí)中學(xué)校長(zhǎng),張桂梅同志!
相關(guān)文章
- 從張桂梅校長(zhǎng)到《我本是高山》,之二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藝
- 在現(xiàn)實(shí)的共產(chǎn)黨人中,確實(shí)存在著具有堅(jiān)定的共產(chǎn)主義理想信念的人
- 不理解共產(chǎn)黨人的人,塑造不出真正的英雄形象
- 四評(píng)《我本是高山》:以共產(chǎn)主義理想信念教育青年人
- 警惕別有用心的人揮舞“極左”的大棍企圖將社會(huì)主義引入歧途
- 三評(píng)《我本是高山》: 對(duì)批評(píng)的批評(píng)—為什么把一個(gè)基于偉大共產(chǎn)主義信仰的故事矮化為基于愛(ài)情的故事?
- 《我本是高山》與武訓(xùn)傳是意識(shí)形態(tài)教育領(lǐng)域激烈階級(jí)斗爭(zhēng)
- 對(duì)《我本是高山》的爭(zhēng)論應(yīng)該再激烈些,求得徹底澄清思想混亂
- 再評(píng)《我本是高山》:犯了幾個(gè)致命錯(cuò)誤
- 譚吉坷德|從《我本是高山》讀懂胡錫進(jìn)
- 國(guó)產(chǎn)電影的氣質(zhì)為什么越來(lái)越“猥瑣”?
- 真正的主旋律猶如太陽(yáng),最怕他們的是魑魅魍魎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yùn)行與維護(hù)。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