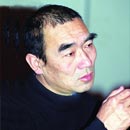大約是在1984年,記得是一個文學雜志召開的會上。我發言時不知為什么幾次提到了“反體制”這個詞。散會后大家坐在一輛面包車里,我聽見后排兩位老前輩在低聲交談:“他說的是什么?反……旗幟?什么叫反體制?”
那一刻的記憶一直未被我忘。雖然今天若說給人聽,怕已沒有幾人會相信。那時在中國“體制”一詞尚聽著拗口,我也不過是因為聽多了罔林信康吼叫的歌,心里哼著“我乃睜開了眼的反體制派”,發著言它順口溜了出來。是的,哪怕經過全面戰爭的“文革”,知識分子的體驗,大都也只是體制內的悲歡離合。
如今不同了。無論手機電腦,只要敲擊tizhi,第一個蹦出來的就是它。如今,簡直國民已被劃分為體制內與體制外兩大族群,從出租車司機到打工農民,對這個詞的體會都會入木三分。
一、
不能以詩人為例談論體制問題。尋找例子,也許挑選考古會更有意思。因為考古,它既是象牙塔學術的頂端象征,又與“田野”上生息的百姓耳鬢廝磨。在某些時刻,民間百姓與專業學者,也即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人——與古代環境與遺跡之間的距離,是一樣的。
不拘泥于考古領域,但是用考古學的方法,卻可能把文明探求的人流,歸納出若干個類型:
第一種人本身就生活在文明內部,或文明共同體的核心里。也許他們就是耕讀鄉里的農民,一代代從“文化”跟前走過,每天捉摸其中的奧妙。如今他們已有了余裕買書上網,并啃完了磚頭般厚重的大部頭。當腦際朦朧浮現的某種感悟、異議、觀點成為沖動時,他們決意進行表達,試圖描述自己理解的文明。
民間的文化內涵,為生長于斯的本地人、農民兒子,也被每日穿行其間的路人熟知。如馬克思所說,以前他們不會表述自己,對他們擁有的文明的解說,總是由外人代言:情報人員、軍人、學者,總之是由職業或專業的人員捉刀代筆。對他們的解說,并漸漸變成專門的知識,在課室里教授,更成了學府的梁架。
第二種是專業分工的產物。求俸及學,因職從業,全因躋身于體制之內,踽踽終老于大傘之下。不問智愚,皇糧味美,他們宛如水銀瀉地,占領遍及每個縫隙。“國際交流”多了以后,我發覺有些“老外”的大學系主任,很像電影里的納粹軍官,一手握生殺大權,眾教師噤若寒蟬。要命的是他(她)退休無期,一個系只能仰望蒼天盼解放。是為體制內學者之歐美類型。但還是中國類型的陣容最龐大:本來社會的細密分工已經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結果,但這兒還有半殖民地的貧血基因,以及社會主義大鍋飯煮糊后倒不掉的鍋巴,所以,世間潮流一旦附庸資本,他們便從偽學的塹壕里蜂擁跳起,向著金錢與權勢倒戈。三十年河西,當年言必稱馬列的他們,早已是資本言說的鐵桿。其間抄炒欺盜,不知生產了多少印刷垃圾。但是極目眺望,豢養的體制尚在迅猛膨脹,這一類型的繁殖,還正方興未艾。
毋庸贅言,專業分工之內也會造就少數的佼佼者。但是,從宏觀的歷史觀察,從已被揭破的東方主義,到死賴茅坑的低質學術,繁衍孳生的體制內知識,已被推到了歷史批判的前臺。
至于第三類型則是一種理想;他們或身在文明遺址之外,也并非由于薪俸和職業使然,而是出自天然的氣質,從對文明的深愛抵達對于文明的忠誠,處于愛好與天性而導致一種宗教式的、文明之子的發現,這樣的例外當然也一直在接續,何止不受職場體制的限制,他們乃是知識分子中的巨人。
總結這幾種類型的人與學術,需要等到這個時代結束以后,上述三種都已徹底成型、并顯示出本質的真正區別之后。今天我們能做的,只是觸碰充溢的現象,提醒傾向中的警示。
二、
河南的民間考古學者馬寶光,是我熟悉的一個身在體制之外,求學于考古域內的人。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因政治的災難,迎受了全家下放農村的人生厄運。恰是在文物蘊藏豐滿的河南農村,他不僅見識了青銅器和畫像磚、古城址和古遺址的模樣,還邂逅了一位落難的考古學家,從而對考古學粗略入門。
他癡迷考古的程度,讓人難以置信。我和他是一對朋友,十數次結伴游走。常常是一塊走路時,他突然失去了蹤影。他像只山羊,不是爬上了半山,就是跑下了斷層,撥拉尋覓,不分公園荒山,總要找到點什么文物。那一年我倆在潼關的舊城,我只是想沿古道走一走,他卻爬到城墻上挖陶片。還有一次在安陽殷墟,我隨著參觀遺址公園的游客溜溜達達,他卻不住地在草叢路邊尋找。我在一邊澆涼水:從李濟到夏鼐,這土早被挖了三百遍了,你以為還剩下什么等著你么?他卻說:上次我只用了半天功夫就找到十幾片甲骨,其中好幾片帶字的!
我被噎住。他又說:下次再來,咱順著這條洹水走一遍。我保證找出點東西給你看!……不能不感慨,他對考古的著迷,遠遠超過了我這退役的考古隊員。
第一次,他把自印的《玉飾花紋》拿給我看。我連說沒價值:你愿意弄這個也可以,但別吹牛說什么學術。河南老地主家里的玉鎖,年代一樣的清末民初,紋飾一色的吉利花紋,有啥研究頭?
但看見他第二次印出的《源匯印譜》,我暗暗吃驚了。從戰國到元明,他居然收集了三百余方古印。不說那些戰國印和漢印,只數人所未聞的元代八思巴文印章,居然就超過了十方之多!我幾乎看見了研究八思巴文的學者、比如我在民族所的老所長照那斯圖先生的興奮表情。若是聽說馬寶光并無收藏的財力,這么稀罕的文物也只是過手過眼,一旦拓片完成,原物便不得已出讓,以求收購新的發現品——他們一定會驚訝。
他的興趣與他的局限并存。若那些珍貴的八思巴文印,他大咧咧注明“印文不識”四字后便擱置一旁,視線集中于印章的源流,以及美術的角度。我讀著他那本自印書的前言,也漸漸感到八思巴文確實不妨留待他人詮釋。確實,一冊在手,讀者就能了解印章的起源、鈕制、印的用法、名稱的變遷、印文的布局、治印的技法、書體和刀工,并能從三百古印中獲得藝術的享受。雖然只是通俗常識,也是必要的工作。
他的功夫,介于鑒賞家、收藏家、發現者和研究者之間。雖不能實行大規模的田野發掘,但河南豐富的文化遺址,以及民間流通的文物數量,不斷豐富著他對青銅玉器漢磚元瓷及楚城漢墓史地傳承的眼光。平日他以各種生計解決溫飽,再以更大熱情,聽由遺存的引導,追蹤古代的奧秘。無從言及名利,也不與工資有緣,他身在體制的機構之外,卻以一廂的鐘情,朝著考古的奧深鍥而不舍。
我曾暗中感慨,他的行為和方向大概是民間求學者共通的:一種天性令人贊嘆,但難得抵達學術的高度。愛好和癡迷都是一廂情愿,雖然樂在其中,但難以與專業人員形成角力。
但馬寶光似乎不服我的斷語。他不只年復一年進行考古的游擊,而且大膽地踏入了研究。
轉述則嫌紙短角多。那一年我們從河北曲陽出關,住在長城下的小店里。深夜披衣對坐,他給我細說了他對魚紋的見解。
簡言之,對從仰韶彩陶到漢畫像磚上遍布的,或濃彩勾描或成批燒制的三角紋、十字紋、米字紋、菱形紋,以及被解釋成森林、睫毛、七星的種種紋飾,他以“魚紋”的觀點,提出了一個有破譯意味的解釋。
他以為:古代人住居的條件是傍河。沿河而居的目的,除了飲水之外是為了食魚。古代人群攝取蛋白質的重要途徑,是捕魚而食。魚不可思議的繁殖力,為古代人群須臾不可離棄、由衷喜愛甚至進而崇拜。于是,多個魚頭朝一個方向排列(<<<<)、兩對魚對頭排列(X)或多條魚攢頭環列(※)的種種抽象化圖案,就成了古代最重要的一種裝飾思路。。
他說的紋飾,確實早已被人司空見慣,至于我則如同視而不見。我沉吟著,想著怎么給他出難題:“怎么覺得好像聽說過?會不會早就有人這么提出過,而你忘了在哪兒讀來的了,后來當了自家發現?”
并非只是抬杠。只要排除了我說的可能,他就算出色地提出了一項見解,給考古和人的知識做出了一個貢獻。
近年馬寶光集中全力突擊的,是河南淺山區大地上的一種巖刻。確實,大地上有一些文化現象,或許屬于神秘的范疇。它們與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相近相遠遙遙呼應,引誘人的靠近又否決人的深究。民間學者最是對這一類問題深懷興趣。混沌大地上怎么會到處都留下了這種鬼斧神工呢?
他們幾乎想直接把天書一語寫進文章,而學術界則審慎地挑選了諸如巖刻等詞來描述。“巖刻”一語是個保險的詞,但是嚴謹在面對造化的豐富時,其實只是無計無策的表達。我雖身處兩難之間,為行文方便姑且也直呼天書。因為幾乎所有人都覺得那些鑿在一道道山脈兩翼、在人跡罕至的山腿一行行詭秘排列的石上凹穴,實在過于匪夷所思。尤其在泌陽縣羊冊鄉山麓,一頭巨大的石羊身上,滿披符咒般的坑點,渾然令人不得不聯想天書。但是冷水懸于頭上:因為很難解決對這頭大羊的斷代。中原大地風俗古老,但古風更使判斷年代加了一道迷障。在擂鼓臺,我倆目擊了當地以亡童獻祭的遺風。那么凹穴會不會也是今人的鑿刻呢?說不清刻下天書的究竟是夏商的神官還是民國的地主,只能感到民間與大地上,藏著一脈相承的思路。
馬寶光千里單騎的考古,宛似到了最后的沖刺。他坐著長途班車,指揮一伙原來在縣城街上閑逛、現在隨他迷上了考古的青年,逐縣排查,拉網搜索,尋找天書。方城、淅川、南陽——九個縣市的方圓里,幾乎隨人足跡所至,天書便破土而出。瞪著呈現眼前的天書,小報忙轉載,政府也興奮,后來居然是哪個縣市發現了天書群,馬寶光便被該縣授予名譽縣(市)民稱號。
實在難以想象,就在河南省的西南一隅,體制外的考古,居然被一個人搞得轟轟烈烈!
就這樣,積累日漸堆積,一介民間百姓,居然編輯了一套六冊本考古文叢。當然“出版”對民間的表述常是拒絕;唯因在印刷術的故鄉如今印刷術終于普及,才使他能夠找到簡陋的小印廠,白紙切邊,藍紙函套,把沖決欲出的悲愿,終于印成了書。
三百方從戰國到元代的古印、數百種漢磚紋飾、數百種畫像磚圖案、一冊民間的玉器拓本、一套瓷器圈足的青花藝術、以及一輯中州大地的天書或巖刻——每一冊都附有這一領域的入門導論。隨心所欲,直覺大膽,雖然端詳著似不甚像論文,但每篇都是一氣呵成,淋漓痛快,毫無八股。他的涉及,有些是對鑒賞的導讀,有些則已是研究的攻堅。如前述對從彩陶到漢磚紋飾中“魚紋”起源與抽象的研究,就已經屬于學術的一家之言。
三
他在北京大學豪華的演講廳里,克制著河南的家鄉土語,別著勁用普通話講解魚紋的演變。一旁靜聽的我,琢磨著他講的內容,更體會著他存在的意味。那一天他在北大,講得遠不如我倆在王屋山、雁門關、五丈原等地夜宿十元小店促膝而談時,一口河南話,講得那么精彩。
一邊旁聽的我,感到了一種沉重。他的胃口和他的推論,都已經愈來愈大,他闌入的領域,也愈來愈艱深了。他的查索,已經從《左傳》的印章記事“問璽書追而與之”,一部跳躍到難懂的《尚書》甚至撲朔迷離的“河圖”。這令我不能不擔心他的能力。
“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畫八卦,謂之河圖。”——這已不單牽扯學術的淵源,也糾纏著古代的奧義。他具備甄別、看破、梳理的能力,面對如此題目,達到科學而非隨意的把握么?
但沉吟的原因尚不在此。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云:
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凡時代思潮,無不由“繼續的群眾運動”而成。所謂運動者,非必有意識、有計劃、有組織、不能分為誰主動誰被動。凡參加運動之人員,每各不相謀,各不相知,其從事運動時所任之職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異。……其中必有一種或數種之共通觀念焉,同根據之為思想之出發點。……此觀念者,在其時代中,儼然“現宗教之色彩”。
或許梁啟超設想和鼓吹的,是一種不受體制桎梏的束縛、推動文化昂進的時代思潮。我們此刻面對的,確是那么新鮮的思潮么?我們如今身處的,是那樣的一個時代么?
至少在文學界,我們已看膩了一代代人的出世、成名、異化與腐爛。他們的質地中,先天缺乏抵御體制侵蝕的基因。他們中的一部分,無疑將可悲地被淘汰,沉入中國文人逍遙與墮落的泥河。
他們常把修辭的小技,錯當了思想的發現。他們決絕的姿態,多是“早期”的化妝。他們慣以文學的主觀,掩飾對客觀世界認知的無能。他們猛烈地抨擊權威,只因憤慨自己地位的低賤。他們總是滿腔怨憤,其實從來不為他人痛苦。他們以為一己私臆的發泄,就是人性的解放——他們尤其膜拜西洋的八股,燕人學步,尋章弄句,把西方價值認作文學的宗教。
體制外的考古,與這樣的命題有關么?
那一天我作為講演會的評議人,在會場也講了幾句。我在贊賞北大考古諸學兄為民間學者提供發表場所的舉動之后,更呼吁聽眾對馬寶光的質疑。因為我深知,體制既然能存在久遠,乃因其積累的深度與規范,馬寶光其實把自己擺上了尖銳的學科駁難面前,其嚴厲程度,也許他自己還不能想象。
無論如何,一個終日為五斗米操勞煩惱的民間人,居然在中原大地上奔波思考,不僅成就了一套考古論叢,時而還向象牙塔內的學術填空補白,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有意味的事。
混雜于馬寶光廣泛也可以說雜蕪的成績之中,泥土氣息,農民味道,非專業感,無疑都在所難免。但我更想留意的,是其中的一股真摯和一種體制外的意味。是的,在人心浮躁的今天,在印刷垃圾瘋狂生產的時代,如此真摯地涌動于體制外的潮流,應該受到注意了。
誰能盡知這一次涌動的命運,以及它未來的趨勢呢?
體制的引誘何等強大!公務員,鐵飯碗,幾乎可以說,中國人的目標不過如此,多數話語權威的秘密,也不過如此。其實國民已經幾乎被劃分成體制內外兩大類,滲透推搡,在矛盾中等候著下一次危機。
可以斷定的是,今日體制外奮斗大軍中的一部分人,將會對腐朽體制采取恭順姿態。瀏覽著個人奮斗的故事可以知道,挑戰體制往往不過是可悲的作態,不過是躋身體制的手段而已。
但真摯的初衷,確是理想的重點,所以梁啟超說,它“儼然現宗教之色彩”。
既然敢于置身體制外的追求,就應該斷念于出世的榮耀。馬寶光和他身后遍及于各種領域的奮斗者大軍,能守住這一姿態的尊嚴么?否則他們將玷污自己的初衷和意義,再次跌入常見的沉淪。
但同樣無疑,存在著真有大志的人。
或許經由他們的努力,病入膏肓的知識界會獲得換血,中國會出現新的文學、新的學術和嶄新的知識分子。或許他們將推動真的時代思潮,更新資本控制以來的知識體系,迎來所謂文化昂進的時代。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