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讀】近年來,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經(jīng)濟(jì)的興起催生了“零工經(jīng)濟(jì)”,使“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成為一大熱點(diǎn)話題。但“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不僅僅是平臺(tái)經(jīng)濟(jì)的產(chǎn)物,要了解其形成原因,就要探討它在中國經(jīng)濟(jì)中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
著名歷史社會(huì)學(xué)家黃宗智指出,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模式實(shí)際上是從西方引進(jìn)的,但在中國的規(guī)模超過了西方,原因是中國的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與西方的相比,實(shí)際上有著深刻的社會(huì)歷史背景——明清以來的人地壓力和城市-農(nóng)村戶籍二元制度,共同形成了“半工半耕”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模式;改革開放以后,大規(guī)模的、離土又離鄉(xiāng)的“農(nóng)民工”開始進(jìn)入城市打工,減輕企業(yè)人工費(fèi)用壓力的需求導(dǎo)致了農(nóng)民工的非正規(guī)待遇。結(jié)果,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雖然歷史性地推動(dòng)了經(jīng)濟(jì)快速發(fā)展,卻也帶來了社會(huì)不平等。
今天,非正規(guī)工作條件已經(jīng)成為中國最普遍的就業(yè)條件和情況,其大規(guī)模興起的重要?jiǎng)恿χ唬钱?dāng)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權(quán)宜決策。目前,國家明確轉(zhuǎn)向“共同富裕”的長遠(yuǎn)社會(huì)主義目標(biāo),有望逐步克服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的負(fù)面影響,實(shí)現(xiàn)中國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長遠(yuǎn)可持續(xù)發(fā)展。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原題為《中國的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僅代表作者觀點(diǎn),供諸君思考。
中國的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
▍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在中國的興起及其影響
對“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這個(gè)用詞,大家會(huì)有不同的理解。我在《實(shí)踐社會(huì)科學(xué)與中國研究》第三卷《中國新型的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實(shí)踐與理論》這本書中認(rèn)為,它是一個(gè)相對“正規(guī)經(jīng)濟(jì)”而言的概括。正規(guī)經(jīng)濟(jì)指的是城鎮(zhèn)就業(yè)人員中具有勞動(dòng)法律保護(hù)的勞動(dòng)人員的工作狀況。對中國來說,在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幾乎所有的職工在工作條件層面都有上世紀(jì)20年代革命時(shí)期以來形成的社會(huì)主義的勞動(dòng)法保障,譬如8小時(shí)的工作日,超時(shí)要多付半倍工資,還有一定的社會(huì)保障(工傷、患病、失業(yè)、退休等保險(xiǎn))。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則是相對正規(guī)經(jīng)濟(jì)而言的工人和工作條件,沒有同樣的工時(shí)限制,沒有失業(yè)、退休、工傷等社會(huì)福利或保險(xiǎn)。
上世紀(jì)60年代,聯(lián)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率先使用了這個(gè)用詞和概括,目的是提倡為勞動(dòng)人民提供法律保護(hù)和社會(huì)保障。當(dāng)時(shí),大部分發(fā)達(dá)國家的工人都有這些保障,“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在此主要指后發(fā)展國家的工人工作狀況。國際勞工組織因此還在1969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jiǎng)。
2002年,國際勞工組織發(fā)表了一個(gè)比較權(quán)威的關(guān)于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的研究顯示,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在發(fā)展中國家的規(guī)模已經(jīng)達(dá)到所有工人的一半至四分之三的比例:在亞洲(不包括中國)達(dá)到三分之二,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達(dá)到四分之三,在拉美和北非達(dá)到二分之一。
由于革命傳統(tǒng)和社會(huì)主義計(jì)劃經(jīng)濟(jì),在改革之前,中國主要是正規(guī)經(jīng)濟(jì)。當(dāng)然,仍然有臨時(shí)工、民工、季節(jié)工、協(xié)議工、合同工等,實(shí)際上屬于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的用工方式,但規(guī)模較小,與改革之后的情況很不一樣。
20世紀(jì)80年代,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興起,大量“農(nóng)民工”“離土不離鄉(xiāng)”地在新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工作。之前,他們習(xí)慣的是集體時(shí)期的工分制度,進(jìn)入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工作之后,初始時(shí)期有的仍然按工分來計(jì)算報(bào)酬,后來進(jìn)入了拿工資的制度,但完全談不上當(dāng)時(shí)國企工人那樣的正規(guī)待遇和條件。由此,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在中國開始興起。
從20世紀(jì)90年代起,大規(guī)模的離土又離鄉(xiāng)的“農(nóng)民工”開始進(jìn)入城市打工,他們幾乎全都是在非正規(guī)待遇下工作的。
2010年以后,兩種農(nóng)民工的總數(shù)已經(jīng)將近3億,占到城鎮(zhèn)所有從業(yè)人員的四分之三,中國成為全球非正規(guī)就業(yè)占比最高的國家之一(這里,我們當(dāng)然也應(yīng)該加上20世紀(jì)90年代后期,在國企“抓大放小”的過程中“下崗”的四五千萬工人)。今天,非正規(guī)工作條件已經(jīng)成為中國最普遍的就業(yè)條件和情況。
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甚至對正規(guī)經(jīng)濟(jì)也造成一定的去正規(guī)化壓力。部分由于其強(qiáng)大壓力,如今,即便是較大規(guī)模的正規(guī)經(jīng)濟(jì)的企業(yè)和公司,有不少都采用996的工時(shí)條件和運(yùn)作方式,不再遵循舊勞動(dòng)法的規(guī)定。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大規(guī)模興起的重要?jiǎng)恿χ唬耸菄也杉{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戰(zhàn)略決策。
非正規(guī)就業(yè)對中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加強(qiáng)了中國招引外資的吸引力,使中國成為全球投資回報(bào)最高的國家——年利潤率達(dá)到20到25個(gè)百分點(diǎn),三四年便可以翻一番,促使中國成為“全球工廠”,推進(jìn)、加快了中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同時(shí),它也減輕了中國企業(yè)(包括國企)在人工費(fèi)用方面的“負(fù)擔(dān)”,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它們更強(qiáng)的競爭力。
但它也造成中國的貧富不均,加大了勞資間的差距和矛盾,促使中國在三十年內(nèi)從全球比較平等的國家之一轉(zhuǎn)化為全球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之前,中國革命較大程度上克服了中國的貧富不均問題(當(dāng)然仍有一定的城鄉(xiāng)差別)。改革開放后,基尼系數(shù)一度顯示中國貧富不均非常嚴(yán)重,乃是社會(huì)不公問題比較嚴(yán)峻的國家。
我們也要看到,近幾年來,國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確實(shí)已經(jīng)展現(xiàn)了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權(quán)宜決策,轉(zhuǎn)向國家憲法和黨章一再申明的追求“最大多數(shù)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社會(huì)主義理念。當(dāng)然,這個(gè)過程的快慢、具體做法、運(yùn)作方式和機(jī)制,都尚待觀察。
▍半工半耕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
中國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的興起要結(jié)合“半工半耕”農(nóng)業(yè)模式的興起來認(rèn)識和理解,兩者其實(shí)是同一現(xiàn)象的兩個(gè)方面。
我們要從中國的人地壓力說起。明清時(shí)期,按照當(dāng)時(shí)的技術(shù)水平,一個(gè)男子能夠耕種10到15畝的耕地,但實(shí)際的勞均耕地面積卻一直在遞減,到清代后期才約6、7畝,到新中國成立時(shí)期更縮減到勞均才約4、5畝地。
怎么辦?明清時(shí)期的一個(gè)辦法是轉(zhuǎn)入按畝更高產(chǎn)出的農(nóng)作物生產(chǎn),最普遍的是從勞動(dòng)投入已經(jīng)高度密集的水稻轉(zhuǎn)入更加密集的棉花-紗-布的生產(chǎn),尤其可見于長江三角洲地區(qū)。棉花-紗布生產(chǎn)按畝需要18倍于水稻的勞動(dòng)投入,約180天相對10天。人們之所以這么做,是因?yàn)閱我划€耕地就能獲得3、4倍于水稻的收入。在長三角,它甚至擴(kuò)展到當(dāng)時(shí)稱作“衣被天下”的程度,棉農(nóng)生產(chǎn)的剩余棉布與糧農(nóng)生產(chǎn)的剩余糧食之間的交易成為當(dāng)時(shí)市場經(jīng)濟(jì)中的最大宗,占到總額的五分之四。而農(nóng)戶能夠承擔(dān)那么勞動(dòng)密集性的生產(chǎn),主要是依靠家庭的輔助勞動(dòng)力——婦女、老人和兒童(這些勞動(dòng)力沒有太大的“機(jī)會(huì)成本”,不容易在家庭之外找到工作),這就形成了當(dāng)時(shí)種植業(yè)+副業(yè)性的紡紗、織布的緊密結(jié)合。它是以高密度勞動(dòng)投入和不成比例的收益來組成的,我稱之為“內(nèi)卷化”,即沒有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提高的增長;而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的提高乃是“現(xiàn)代發(fā)展”中至為關(guān)鍵的變化,所以,我又稱之為“沒有發(fā)展的增長”,含義有點(diǎn)像今天的996非正規(guī)用工。
這一切意味著,中國(即使是在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期)農(nóng)業(yè)中其實(shí)存在著巨大的勞動(dòng)力相對過剩問題,達(dá)到總勞動(dòng)力的大約三分之一到一半。這就是農(nóng)民外出打工的一個(gè)最基本的背景和原因。
它造成了一個(gè)和西方發(fā)達(dá)國家歷史很不一樣的現(xiàn)象。農(nóng)民進(jìn)入城市打工,不是簡單地像在西方先進(jìn)國家那樣,是完全離開農(nóng)村而進(jìn)入城市的城鎮(zhèn)化,不是農(nóng)民簡單轉(zhuǎn)為工人的工業(yè)化,而是形成了一種中國特殊的“半工半耕”社會(huì)形態(tài)。農(nóng)村戶籍和城市戶籍的二元?jiǎng)澐种贫确从车恼沁@樣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一定程度上也在維護(hù)、延續(xù)這種形態(tài)。如今,幾乎所有農(nóng)村家庭都有人在外打工,一開始主要是離土不離鄉(xiāng),隨后一半以上是離土又離鄉(xiāng)。在外打工的多是年青一代,年老的(也有中年的)留鄉(xiāng)。
從全球視野來看,這是個(gè)比較獨(dú)特的中國社會(huì)形態(tài),既源自它的基本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實(shí)際,也源自它的戶籍制度。
這一基本實(shí)際已經(jīng)導(dǎo)致一些大家意料不到的后果,我在《中國新型的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這本書里有深入討論。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稱作中國現(xiàn)代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中的“新農(nóng)業(yè)革命”,主要體現(xiàn)為新型高附加值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特別是高檔蔬菜、水果、肉禽魚養(yǎng)殖和蛋奶的生產(chǎn)。最典型的是1、3、5畝的小、中、大拱棚蔬菜生產(chǎn),它既是一種資本投入相對密集的(拱棚設(shè)施、化肥、良種)農(nóng)業(yè),也是需要?jiǎng)趧?dòng)密集投入的“資本與勞動(dòng)雙密集化”的生產(chǎn)。
它的興起反映的是,隨著收入的提高,人民在食物消費(fèi)上的轉(zhuǎn)型——從原來糧食:蔬菜:肉食的8:1:1型轉(zhuǎn)入香港、臺(tái)灣等地區(qū)的4:3:3型。市場的需求導(dǎo)致了農(nóng)民生產(chǎn)決策的轉(zhuǎn)化。如今,這樣高附加值農(nóng)業(yè)的生產(chǎn)已經(jīng)達(dá)到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的三分之二,農(nóng)業(yè)耕地的三分之一。這是農(nóng)業(yè)中一個(gè)巨大的變化。
這個(gè)變化與半工半耕的社會(huì)形態(tài)密不可分。新的資本來源實(shí)際上主要是農(nóng)民打工的收入,尤其是“離土不離鄉(xiāng)”的農(nóng)民工的打工收入。他們不僅將非農(nóng)收入投入家庭農(nóng)業(yè),還會(huì)在農(nóng)忙季節(jié)回家?guī)兔κ崭睢N液秃献髡咴谶@方面的研究證明:來自小農(nóng)戶家庭自身的投入超過國家的投入和資助,也超過公司型農(nóng)業(yè)的投入。
最近十來年,還出現(xiàn)了一個(gè)比較意外的變化。如今,大田農(nóng)業(yè)——主要是糧食種植——已經(jīng)越來越多地使用機(jī)械,在耕播收中的比率已近四分之三。這個(gè)變化背后的動(dòng)力也來自“半工半耕”的基本實(shí)際:外出打工收入超過了雇用機(jī)耕播收服務(wù)的成本,農(nóng)民因此愿意花錢雇用機(jī)械服務(wù),從而推進(jìn)了農(nóng)業(yè)機(jī)械化。
高附加值的新農(nóng)業(yè)和大田農(nóng)業(yè)的機(jī)耕播收,乃是中國農(nóng)業(yè)近幾十年中最突出的變化和發(fā)展。
此外,還有一種值得特別提到的變化:如今半工半耕狀態(tài)不僅可見于同一家庭中的不同成員,更可見于同一位農(nóng)民個(gè)人。正是這種新興狀態(tài)促使第三次全國農(nóng)業(yè)普查將農(nóng)業(yè)從業(yè)人員重新定義:從之前的從事農(nóng)業(yè)6個(gè)月以上改為從事農(nóng)業(yè)1個(gè)月。
我這里要特別突出一個(gè)要點(diǎn):人們習(xí)慣使用“三農(nóng)問題”這個(gè)詞,但這個(gè)詞更多指出的是“問題”,而忽視了小農(nóng)戶對中國農(nóng)業(yè)的現(xiàn)代化做出的巨大貢獻(xiàn)。“三農(nóng)”其實(shí)不僅是個(gè)“問題”,也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一個(gè)基本的動(dòng)力。
當(dāng)然,如今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仍然巨大。小農(nóng)戶收入提高了,但城市的收入上升得更快。我們只有認(rèn)識到這個(gè)基本實(shí)際,才能真正設(shè)想中國農(nóng)村和中國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的未來。
▍從舊勞動(dòng)法到新勞動(dòng)合同法
從勞動(dòng)法律的角度來看,改革時(shí)期至為重要的轉(zhuǎn)變是2007年新勞動(dòng)合同法的頒布,它基本完全取代了之前的勞動(dòng)法。其中的變化,尤其從勞動(dòng)者的角度來考慮的話,不能只靠法律條文來認(rèn)識和理解,必須要結(jié)合它在實(shí)際運(yùn)作中的效果來思考。
1995年頒布的勞動(dòng)法仍然保持了革命時(shí)期舊勞動(dòng)法的規(guī)定:包括8小時(shí)的工作日、一周44小時(shí)、超時(shí)要加付半倍的工資、基本保險(xiǎn)和福利,等等。從2007年的新勞動(dòng)合同法開始,越來越多的勞動(dòng)人民被轉(zhuǎn)入基本沒有上述保障的非正規(guī)就業(yè)。如今,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職工已經(jīng)占到所有城鎮(zhèn)就業(yè)人員四分之三的比例。這是最基本的事實(shí)。僅從法律條文來考慮的話,我們看不到這個(gè)實(shí)際。
第一,沒有勞動(dòng)法律保護(hù)的“合同工”名義上被限定為“臨時(shí)性、輔助性或替代性”的職工,表面看來似乎僅涉及較低比例的職工;而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huì)保障部更在2014年提出規(guī)定,企業(yè)要在兩年之內(nèi)使得非正規(guī)臨時(shí)工的比例不超過10%。但實(shí)際上,情形完全不是這樣。如今,被非正規(guī)地按照新勞動(dòng)合同法來雇用的職工,已經(jīng)占到所有職工的四分之三,并且居高不下。
第二,新勞動(dòng)合同法比較“微妙”地提出要區(qū)別“用人單位”和“用工單位”。用人單位乃是實(shí)際上的雇用單位,但與勞動(dòng)者簽訂合同的不是用人單位而是用工單位。后者一般僅僅是個(gè)中介公司,他們替代了真正的生產(chǎn)實(shí)體公司和勞動(dòng)者簽訂合同。邏輯上,這些中介公司只需負(fù)責(zé)合同規(guī)定的條件,只管“工”但不管“人”,因此談不上福利和保障。
第三,在舊勞動(dòng)法下,雇用單位需要對勞動(dòng)者人身負(fù)責(zé),包括工作安全、合理的工時(shí)和超時(shí)的補(bǔ)貼、醫(yī)療費(fèi)用、退休等各種保護(hù)工人的規(guī)定,這是舊勞動(dòng)法的基本目的和出發(fā)點(diǎn)。新的合同法則從完全不同的原則和規(guī)定出發(fā):名義上,工人和勞務(wù)派遣公司簽訂的是一個(gè)雙方平等的自愿協(xié)議,但它的條件不附帶福利和勞動(dòng)保障,僅附帶合同中所認(rèn)定的條件,實(shí)際效果是一舉廢掉了之前的勞動(dòng)保障。
一般勞動(dòng)人民并不很了解其中的奧妙,或者,即便了解,但在找工作的時(shí)候,權(quán)力基本全在雇用方,受雇者不會(huì)也不大可能提出疑問,因?yàn)榭赡軙?huì)因此不被雇用。在較普遍的“霸王合同”的情況下,被雇人要到簽訂合同的最后時(shí)刻才能看到雇用方使用的格式化合同,有的甚至根本就看不到,完全談不上討價(jià)還價(jià)。
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數(shù)據(jù)庫具有大量的實(shí)際相關(guān)案例。我聚焦于新勞動(dòng)合同法主導(dǎo)下涉及勞務(wù)派遣工的實(shí)際案例做了大量研究,上面的概括就是根據(jù)相關(guān)系統(tǒng)抽樣的案件得出的結(jié)論。
客觀來說,國家之所以采用這樣的用工法律,一個(gè)非常重要的考量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權(quán)宜性戰(zhàn)略決策,這一決策偏重企業(yè)方遠(yuǎn)多于工人方,為的是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包括招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來協(xié)助推動(dòng)中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它有意要利用中國極其豐富的勞動(dòng)力,尤其是農(nóng)村的勞動(dòng)力——“農(nóng)民工”—— 來協(xié)助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快速發(fā)展,并且,確實(sh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對國家來說,法律絕不僅僅是衛(wèi)護(hù)權(quán)利的規(guī)定,更是協(xié)助國家行政管理的手段。使用勞動(dòng)合同法既是為了使企業(yè)達(dá)到更高的收益、更快的發(fā)展,也是要通過法律來系統(tǒng)地規(guī)范化這樣的用工方式和戰(zhàn)略決策。
從勞動(dòng)人民的角度來考慮的話,我們從實(shí)際案例可以看到,用舊勞動(dòng)法規(guī)的邏輯和條文來力爭是不會(huì)起作用的。法院已經(jīng)不再支持那樣的舊法律邏輯和規(guī)定。
最近幾年,國家還進(jìn)一步做出了另一司法規(guī)定:只要是“政府主導(dǎo)”的改制,法院基本不受理。這是20世紀(jì)90年代國企“抓大放小”改革、迫使幾千萬職工下崗時(shí)使用過的方法。法院根本就不受理此類勞動(dòng)爭議,國家簡單規(guī)定必須由所涉及的企業(yè)單位自己來解決。
我們可以看到,在新法律的規(guī)定和實(shí)施下,勞動(dòng)者想要憑借法律手段來爭取舊勞動(dòng)法規(guī)定的權(quán)利,完全沒有勝算。要想獲得補(bǔ)償,只能按照新的勞動(dòng)合同法的邏輯和條文來據(jù)理力爭。譬如,簽訂合同的派遣公司違反了合同中的規(guī)定或條件,或沒有按照合同法規(guī)定來改制,沒有遵循合同所標(biāo)明的執(zhí)行條件等。
真正改變這一情況的是國家政策和法律的轉(zhuǎn)向。近幾年,國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確實(shí)已經(jīng)展現(xiàn)了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權(quán)宜決策,轉(zhuǎn)向社會(huì)主義更長遠(yuǎn)的“共同富裕”目標(biāo)。譬如,農(nóng)村的“扶貧”(這里的“貧”只是“赤貧”)工程、鄉(xiāng)村振興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劃轉(zhuǎn)”一定比例的企業(yè)利潤予社會(huì)保障基金等。當(dāng)然,其具體進(jìn)程的快慢、程度、實(shí)施方式等都還有待觀察。一定程度上,國家本身也還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
▍全球視野下的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
勞務(wù)派遣的法理是中國從歐美發(fā)達(dá)國家引進(jìn)的。它的起源,正像中國的新勞動(dòng)合同法所模仿的那樣,主要是用于“臨時(shí)性、輔助性、替代性”的人員,原意是給予企業(yè)、公司在用工方面更大的靈活性,即所謂的“靈活用工”,以臨時(shí)合同的方式來雇用短期的、僅在部分時(shí)間工作(part time)(包括鐘點(diǎn)工、快遞人員、按件收費(fèi)等類型)的工人。雖然如此,在實(shí)際運(yùn)作層面上,其適用范圍也已經(jīng)遠(yuǎn)不止此,越來越多地包括全職、長期用工。其目的當(dāng)然也是要減輕企業(yè)在用工方面的負(fù)擔(dān)。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這一用工模式在英美和西歐的用工比例中已經(jīng)占到20%~25%。
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可以說是伴隨西方近半個(gè)多世紀(jì)以來越來越貧富不均的現(xiàn)實(shí)而形成的。具體來說,上世紀(jì)五六十年代,就業(yè)人員習(xí)慣的是,家里(如工廠工人)僅需有一人就業(yè)便足以養(yǎng)家,并達(dá)到“中產(chǎn)”生活(有房子有車)水平;其后,在20世紀(jì)80年代,則要夫婦倆都就業(yè)才能做到;再其后,則基本上只有上過大學(xué)的“白領(lǐng)”夫婦才能做到了。
在這期間,全社會(huì)工資最高的1%和10%的人收入所占的比例一直都在攀升,“中產(chǎn)”所占比例一直都在縮減,下層收入人士占比一直都在擴(kuò)大。這是種族主義和極端威權(quán)主義的肇因之一。其中相當(dāng)部分人的感覺是,他們的工作都被中國的廉價(jià)勞動(dòng)人員搶去了。這是美國人民反華意識最近再次以相當(dāng)規(guī)模興起的一個(gè)重要原因。
近十年來,研究勞動(dòng)人民的英美學(xué)者普遍采用一個(gè)新的用詞,即結(jié)合“危難”(precarious)和“工人/無產(chǎn)階級”(proletariat)兩個(gè)詞創(chuàng)建的“危難工人”(precariat),來概括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在英美和西歐發(fā)達(dá)國家所呈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
吊詭的是,這套法理雖然是中國從西方引進(jìn)的,但其規(guī)模如今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超過原輸出地。當(dāng)前中國非正規(guī)就業(yè)在所有就業(yè)中占比四分之三,可以說是英美靈活用工理論模式和趨向的放大版。這個(gè)事實(shí)當(dāng)然和中國巨大的農(nóng)村人口和人地壓力直接相關(guān),也和在中國形成的“半工半耕”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和“農(nóng)民工”直接相關(guān)。
“農(nóng)民工”中的“新生代”更像英美的“危難工人”:他們已經(jīng)基本和農(nóng)村隔絕,大多不會(huì)返回農(nóng)村。而且,他們對城鎮(zhèn)工作的預(yù)期也和“危難工人”比較相似,期望未來能夠找到穩(wěn)定的、可以借以安居城市的工作。
但他們的處境要比危難工人危難得多。因?yàn)樗麄兇蠖嗳匀粌H具有農(nóng)村戶籍身份。他們的出路相對更難更窄,基本上必須上大學(xué)才有可能進(jìn)入中產(chǎn)階層。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農(nóng)民工父母為何高度重視孩子們的教育。但是,和美國情況完全不同,目前,農(nóng)民工子女在就業(yè)地(而非戶籍地)上學(xué),還需要繳納不合理的高昂擇校費(fèi)。教育和房子乃是農(nóng)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障礙,亟須改革。
▍國家戰(zhàn)略的轉(zhuǎn)向與我們的前瞻愿景
2018年以來,國家明顯已經(jīng)從改革初期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權(quán)宜決策,開始轉(zhuǎn)向“共同富裕”的長遠(yuǎn)社會(huì)主義目標(biāo)。
首先,2018年,繼“精準(zhǔn)扶貧”之后,國家提出“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規(guī)劃”。后者帶有依賴農(nóng)民的建設(shè)性和主體性的宗旨,提出要建設(shè)村村戶戶通路、通互聯(lián)網(wǎng)的具體執(zhí)行目標(biāo)。目前鄉(xiāng)村道路基本僅通達(dá)行政村,即村委所在地,尚未能夠通達(dá)自然村(即村小組)和家家戶戶。真能做到這一點(diǎn),無疑會(huì)對克服長期以來的城鄉(xiāng)差別問題起到重要作用,能夠糾正以往主要是單向的、由農(nóng)村輸出物品給城市消費(fèi),而沒有相等程度的城市向農(nóng)村輸出物品的模式——這點(diǎn)可見于清代的城鄉(xiāng)貿(mào)易,乃至于新中國成立時(shí)期的城鄉(xiāng)差別之中,一定程度上今天仍然存在。
我們知道,在經(jīng)濟(jì)歷史中,平等互利貿(mào)易——區(qū)別于單向的、不平等的,或榨取型的交易——會(huì)導(dǎo)致雙方的進(jìn)一步社會(huì)分工,加上現(xiàn)代的要素投入,將會(huì)提高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農(nóng)村將會(huì)輸出更多的高附加值農(nóng)產(chǎn)品,購買更多的城市產(chǎn)品。在這方面,發(fā)展空間還很大。以美國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為例:它的高附加值農(nóng)業(yè)產(chǎn)品,主要是蔬果,雖然僅用了全國3.6%的耕地,但其產(chǎn)值相當(dāng)于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的36.8%,也就是說,不止十倍于其耕地使用面積。中國的“新農(nóng)業(yè)”離那樣的水平還很遠(yuǎn),同比才高半倍到一倍。再則是有機(jī)農(nóng)業(yè),美國已經(jīng)占到全球的47%,歐盟則占到37%,中國才6%, 還有很大的發(fā)展空間。
“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規(guī)劃”還提到“縱向一體化”的農(nóng)產(chǎn)品銷售設(shè)施。迄今為止,中國還沒有能夠做到生鮮農(nóng)產(chǎn)品物流冷凍鏈的普及,運(yùn)輸中消耗巨大,遠(yuǎn)高于發(fā)達(dá)國家。在這方面,日本的實(shí)例尤其突出,它設(shè)立了基于農(nóng)村社區(qū)的綜合性合作社(農(nóng)協(xié)),上面加上國家投資建設(shè)的服務(wù)型批發(fā)市場——有冷凍設(shè)施,服務(wù)費(fèi)用較低,產(chǎn)品鑒別精準(zhǔn)、高效,農(nóng)協(xié)產(chǎn)品因此成為具有全國聲譽(yù)的品牌。這些,中國還都沒有能夠做到。
“新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服務(wù)進(jìn)一步發(fā)展,無疑會(huì)給中國農(nóng)民帶來更高的收入,加上靈便的道路和互聯(lián)網(wǎng)連接,將會(huì)大規(guī)模促進(jìn)中國的城鄉(xiāng)貿(mào)易,擴(kuò)大中國自身的國內(nèi)市場,降低對國外市場的依賴,進(jìn)一步縮小長期以來的城鄉(xiāng)差別,推動(dòng)中國經(jīng)濟(jì)整體的發(fā)展。
目前,國家雖然已經(jīng)相當(dāng)規(guī)模地放寬了農(nóng)民遷入三、四線城市的門檻,但尚未徹底取消城鄉(xiāng)間的戶籍差別。無論在生活水平還是教育水平上,差距仍然比較懸殊。何況,大部分農(nóng)民子女仍然被限定于戶籍所在地的學(xué)校,不然便要繳納昂貴的擇校費(fèi),嚴(yán)重限制了城鄉(xiāng)之間的社會(huì)流動(dòng),限制了新生代農(nóng)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再則是鄉(xiāng)村和城市間的福利保障差距,即便是交通事故人命的賠償費(fèi)也有巨大的差別。
以上一切都尚待改良。國家今后在這些方面的改革,雖然在大方向上看來已經(jīng)基本確定,但快慢和具體措施都尚待觀察。
此外,我們之前在重慶市的“實(shí)驗(yàn)”中看到過,由政府出資提供先租后買的廉價(jià)公租房的措施,為達(dá)到條件(工作穩(wěn)定三到五年)的農(nóng)民工提供廉價(jià)、有尊嚴(yán)地進(jìn)入城市生活的道路。此項(xiàng)工程的資本不是國家特殊的投資,主要來自政府為民生而進(jìn)入房地產(chǎn)二級市場的增值。它不是在建設(shè)用地加上基礎(chǔ)設(shè)施的初級階段的十倍增值后便轉(zhuǎn)讓給開發(fā)商,而是由政府本身來為200萬到300萬的農(nóng)民工建造廉價(jià)公租房,并讓其能夠先租后買。它的資金主要來自這個(gè)二級市場的增值,由政府進(jìn)入來獲取又?jǐn)?shù)倍的增值。
2010年,國家相關(guān)的三部委(財(cái)政部、發(fā)改委、城鄉(xiāng)住房建設(shè)部)聯(lián)名認(rèn)可重慶實(shí)驗(yàn)的這個(gè)方面,倡議全國推廣,但后來并沒有大規(guī)模付諸實(shí)施。這是國家今天應(yīng)該重新思考的措施。
今后幾年,中國如果能夠重新依據(jù)這樣的做法為農(nóng)民工提供有尊嚴(yán)地融入長期居留的城市生活的門路,無疑將會(huì)大規(guī)模縮小目前的城鄉(xiāng)差別,大規(guī)模擴(kuò)大農(nóng)村人民在“中產(chǎn)階級”中所占的比例,真正實(shí)現(xiàn)過去人們所虛構(gòu)的“橄欖型”的社會(huì)模式。那樣,不僅會(huì)大規(guī)模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的可持續(xù)增長,還可以真正落實(shí)“共同富裕”的社會(huì)主義理念。
這里應(yīng)該連帶提到,最近二十年來關(guān)于中國城鄉(xiāng)差別和農(nóng)民工問題的研究,較多依賴意識形態(tài)化的西方理論的虛構(gòu)。一個(gè)影響極大的“模式”是:世紀(jì)之交以來,中國便已大規(guī)模邁向西方發(fā)達(dá)國家的“橄欖型”社會(huì)狀態(tài),中間大兩頭小。這一論述依據(jù)的不是實(shí)際情況(例如,2008年以來開啟的歷年的“農(nóng)民工監(jiān)測報(bào)告”所精準(zhǔn)證實(shí)的實(shí)際),而主要得自意識形態(tài)化的西方主流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理論”模式。即依據(jù)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劉易斯(W. Arthur Lewis)的論說,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尤其是亞洲的)雖然具有無限的勞動(dòng)力,但一旦進(jìn)入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轉(zhuǎn)型,便會(huì)達(dá)到勞動(dòng)力資源的最佳配置,進(jìn)入(后來被人們稱作)所謂的“劉易斯拐點(diǎn)”,進(jìn)入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jì)的橄欖型狀態(tài)。
這一論述是在城鄉(xiāng)差別仍然巨大,中國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大規(guī)模擴(kuò)增,農(nóng)民工基本全都缺乏基本社會(huì)保障的現(xiàn)實(shí)中提出的。它把不適用于中國的西方理論勉強(qiáng)移植到中國,實(shí)際上掩蓋了中國過去改革時(shí)期中差別嚴(yán)峻、社會(huì)不平等的基本實(shí)際。
我們需要的不是那種勉強(qiáng)的理論移植和中西等同論的意識形態(tài),而是真正基于中國社會(huì)實(shí)際的概括和符合實(shí)際的有效戰(zhàn)略、政策。我們要直面中國巨大的人口壓力、巨大的城鄉(xiāng)差別,以及巨大的正規(guī)與非正規(guī)經(jīng)濟(jì)間的差別的實(shí)際。我們需要的不是意識形態(tài)化的虛構(gòu)、硬套西方的理論,而是符合實(shí)際、能夠見效的腳踏實(shí)地的實(shí)施方案及其執(zhí)行。中國需要的是為中國將近三億農(nóng)民工謀求能夠真正融入城市社會(huì)、進(jìn)入中產(chǎn)階級的可行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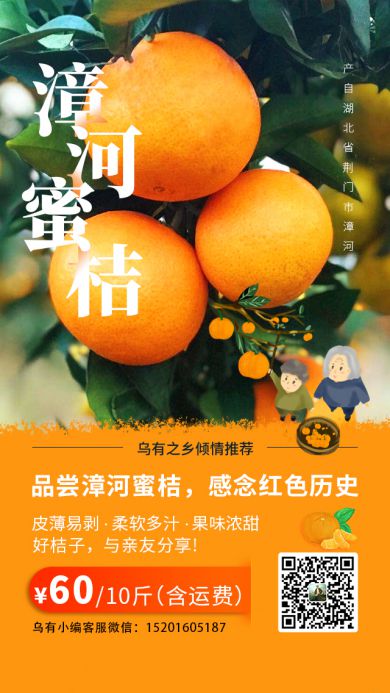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yùn)行與維護(hù)。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