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公式和生產一般的“知”“行”不二
![]()
【總按語·兼答劉光晨】拉法格指出:“數(shù)學家的錯誤也就在于,他們沒有想一想這些公理是怎樣進入人的頭腦的……但是數(shù)學公理不能靠推論證明這件事,還不能證明公理不具有像形狀、顏色、重量或熱量這樣一些物體的性質……只有靠經驗才能暴露……我們只能判明為經驗所證明了的事實,并從中得出邏輯的結論……非歐幾何學,——它的全部命題是相互聯(lián)系在一起并且經過嚴密的推論而得出的,它的定理是同2000年來一直被認為絕對真理的歐幾里德幾何學的定理完全對立的,——是人腦的邏輯的令人驚異的表現(xiàn)。然而,根據(jù)這一點來說,資本主義社會(它是一個活生生的現(xiàn)實,而不是單純的意識上的虛構)可以看作這個邏輯的強有力的證明。這個社會成員被分為敵對的階級;對雇傭工人進行慘無人道的剝削、工人的貧困隨著他們所生產的財富的增長而增長;在物產豐裕中引起饑餓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飽食暖衣的懶漢受到阿諛逢迎的贊揚而受貧困之累的生產者被人輕視,道德、宗教、哲學和科學把社會的無政府狀態(tài)說成是理所當然的;普選權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的少數(shù);總之,在文明的物質構造和思想構造中的一切都向人類的理性挑戰(zhàn),然而這一切都是同完美無缺的連貫性相聯(lián)系的,一切的不正義都可以用精確的數(shù)學從財產權中引出來,這財產權容許資本家有權盜竊雇傭工人所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沿著《資本論》工作路線,只有勞動二重性才能解除“知識的神秘”。所謂土地有機構成、資本有機構成、國家有機構成,都應當是勞動二重性的范疇,既是“知”(歷史理論的生產一般),又是“行”(實踐總公式)。然則,這種純學術研究究竟有什么意義?如果不能實現(xiàn)對哲學工作神秘性的解除,也就不能最終解除思維神秘、邏輯神秘。如果不能實現(xiàn)“知識”,階級本身就是個“概念空殼”。作為階級的物質基礎,技術構成乃是生產方式;正是這個生產方式承載了不同的生產的社會關系,作為各種社會形態(tài)的“經濟(制度)形態(tài)”,支持形成了土地社會和資本社會等等形態(tài)的經濟基礎。種種社會有機構成正是說明生產力和社會聯(lián)系的恰當中介和工具。從而,《資本論》完全不是用“數(shù)量邏輯”來構筑的。拉法格對馬克思方法論的說明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本文的思想努力,即“只有唯物主義,從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根本制止住數(shù)學工具在知識邏輯形式方面的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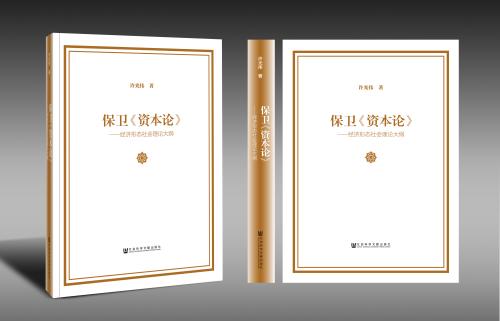
本文系拙作《<資本論>與天人合一
——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的理論續(xù)作
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
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ichao/2019/12/411731.html
![]()
接續(xù):階級社會知識狀況考察之一
![]()
許光偉‖階級社會知識狀況考察之二
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lixiang/2022/01/448436.html

階級社會知識狀況考察之三
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lixiang/2022/01/448697.html
![]()
進一步延伸閱讀:
![]()
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導論
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ichao/2022/01/44889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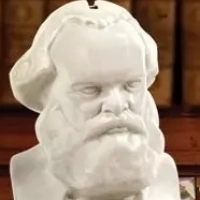
第四部分 總公式和生產一般的“知”“行”不二
(一)
簡單勞動從道路上來,結晶為系統(tǒng)的簡單平均勞動,使得勞動形式定格為總公式實踐意蘊的發(fā)展規(guī)定,同時價值形式成為與之同步的“理論制動閥”(刻畫階級統(tǒng)治的一般邏輯即生產一般理論)的隨行裝置。這是以商品生產(包括由之發(fā)展出來的剩余價值生產)為“化成中心”的歷史世界考察需要用勞動價值論作為對象思維學——實體與工具統(tǒng)一,進行生長方式具象和認識構圖的根本理由。勞動價值論的“知”通常為人熟知,勞動價值論的“行”往往為人們所忽略,而這是階級生產的直接統(tǒng)治結構。立意莫若象,“勞動價值論的成長規(guī)定”(如總體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資本主義簡單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的歷史軌跡如圖2。

圖2 W(L)及其m(L)的歷史化成路線
何謂勞動價值論?如上指出,這個理論其實和唯物史觀與階級斗爭的原理統(tǒng)一有關。圖2展示了“勞動形式(總公式實踐)+價值形式(生產一般理論)”的勞動價值論內部規(guī)定成長構造,它同時適用于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這是個道路規(guī)定,也不斷生出自己的系統(tǒng)運行形式。所謂知行合一定義,始源于此;在知識生產上之所以強調“知”“行”合一,言《資本論》不獨是知識,更重要之處在于其為行動而設。
依據(jù)這一原理,勞動發(fā)展以勞動過程為實踐“總公式”,并決定勞動質的狀態(tài)。在階級社會中,勞動的發(fā)展同時置身于一定的統(tǒng)治形式,如在商品社會形態(tài)中必須具有W(L)和m(L)形式;與之對應的各種價值形式一般在原理上可以統(tǒng)一為個別的價值形式、擴大的價值形式、一般的價值形式、轉化的價值形式,在階級統(tǒng)治關系上即“價值統(tǒng)治”的四重經濟形態(tài)。
所謂元、亨、利、貞,乃統(tǒng)治的行動,對應統(tǒng)治層級的不斷攀升;故而,“轉化的價值統(tǒng)治”也即該運動循環(huán)層級最高意義的階級統(tǒng)治水準,并且將過渡到下一歷史運動循環(huán)類型。這種歷史化成路線同時意味著商品生產的各種歷史總公式必然由勞動過程化來,由于階級統(tǒng)治例如資本的統(tǒng)治,使勞動過程的組成元素各自具有截然不同的發(fā)展形態(tài),以外在方式或異化形態(tài)結合⑧。
【⑧ 正因如此,“馬克思不認為這些抽象是‘暴力抽象’,因為勞動隨著歷史的改變而改變,也趨向于變成簡單抽象勞動。因此,作為理論學家,他只是擴展完成理論,這個改變的過程一直隨著資本的改變而不停地改變著。”(參見《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第71頁,新華出版社2013年出版)】

(二)
正如天人合一內在結構是勞動過程,知行合一的“內在結構”乃有機構成也,是以在總公式實踐和生產一般理論之間展開的一場場“對話”,皆由W(L)及m(L)所化成,所謂邏輯起點范疇說實指知識具象的秩序。價值形式(作為“意”)錨定在實踐行程的深處,化為“言”,就是歷史知識;這樣商品生產的總公式本身必須作為統(tǒng)一的“象”予以對待,正是經由這個總象,“價值形式一般”得以道承。價值一般是個總道的規(guī)定,必具象于道路,然后落實于系統(tǒng)實踐,從階級統(tǒng)治到拜物教統(tǒng)治,完成其歷史使命。作為理論知識,價值形式一般繼而是將“知-行-行-知”形式化,例如,行-知-行、知-行-知可以說是體現(xiàn)在實踐和理論環(huán)節(jié)的“價值形式總公式”。顯然,若言抽象力即范疇法,是就這些總公式的內涵而言的。《資本論》說到底是關于“唯物史觀知識”的具象——所謂“價值形式之變”:由于堅持做到歷史觀上的知行合一,即意味著道路與系統(tǒng)的工作連體性得到貫徹,復由事物生長方式轉向對事物認識方式的追問,于是使研究-敘述方法統(tǒng)一的問題得以解決(見表3)。
表3 《資本論》價值形式之變——知、行對話維度

封之(統(tǒng)之)、建之(治之)是一體的。然則,商品形式代表著階級壓迫的歷史關系形成,是階級關系對象即統(tǒng)治規(guī)定本身,與之不同,價值形式進而表征“統(tǒng)治方式和社會工具”,從工具層面回答階級統(tǒng)治“何以是”和“何以能”。
(三)
表3集中展示了“唯物史觀知識”具象之路,展示由價值形式不間斷的轉化運動所引致的發(fā)生在“總公式”(作為“實踐的行”)與“生產一般”(作為“理論的知”)之間的對話,以及這一對話對該具象途徑的意義。“價值形式何以能變”和“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同一命題的不同方面。既是“知”“行”合一,又是“知”“行”不二,即是說,價值形式必須被理解為知的規(guī)定(如商品、貨幣、資本、職能資本、非職能資本等等)和行的規(guī)定(如產業(yè)資本、資本積累、競爭活動、壟斷活動、信用活動、虛擬資本等等),作為具有理解中介規(guī)定意義的統(tǒng)一。一面是階級,一面是拜物教,理解中介是“階級”(階級客觀)與“拜物教”(階級主觀)的關系統(tǒng)一,是以資本乃“兩面體的規(guī)定”。資本歸根結底是“價值形式”。正是由于采取價值形式統(tǒng)治的緣故,導致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何以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在認知上極難被察覺,——于是乎,“根據(jù)‘拜物教’的概念,馬克思證明了在純粹的資本主義商品化中,社會關系會逐步消失”,換言之,“如果商品是主要的社會經濟連接器,那么商品化程度將決定社會關系客觀化或者物化的程度。”[2]52-53
【[2] 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不僅是知的命題,也是行的命題:圖1中,它作為“價值形式”,既是價值向剩余價值的階級生長關系,又是“拜物教的價格”向“拜物教的利潤”生長意義的規(guī)定形成⑨;圖2中,作為“價值形式”,它將W(L)的化成運動和m(L)的化成運動合而為一。
【⑨ 根據(jù)拜物教的理論,價格系統(tǒng)似乎只能以數(shù)學的方式進行決定,——這其實是暗示了社會關系的完全被商品化。】
價值形式的知識原理具有兩維,導致任何推理哪怕是“辯證推理”都不能實現(xiàn)對“資本內在本質”的揭露。唯一的辦法是將資本邏輯視為從歷史走入現(xiàn)實的“行動邏輯”與“知識邏輯”合成,在意義上進行分裂,通過形成理解張力,實現(xiàn)本質的自我顯露。既作為“理論上的辯證法”,又作為“實踐上的辯證法”,理論與實踐的對峙與互看就成為資本實現(xiàn)自我生長的“歷史世界”規(guī)定。資本的價值形式由對峙與互看的“歷史行動生成”而來,又通過自身特有的階級實踐,直接強化著這種規(guī)定性。然則,總公式最后必然成為價值形式實踐狀態(tài)的具象,而生產一般對應成為價值形式理論狀態(tài)的具象,是為“資本具象”;它們既是資本的構筑元素,又是資本對自身進行顯露的“不二法器”。
“價值形式之變”的實踐根據(jù)是總公式,理論根據(jù)是生產一般;一陰一陽謂之道,使資本“生死歷程”得以全面呈現(xiàn)和展示。實踐的轉化以理論為中介,理論的轉化以實踐為中介,這同時使得《資本論》不可能依照單一路線前進,而必須既按照歷史、又按照邏輯進行。歷史在這里起到了總公式的作用,以至于它和邏輯可以是同一個東西,但是如果否認實踐歸根結底是決定理論的東西、一切理論說到底是“歷史理論”,那么,就很容易把資本邏輯抽象化、形式流程化,忘記了資本原來是從歷史走入現(xiàn)實、又根本是要走向未來即一種歷史過渡的實踐性的東西。說馬克思關于資本所做出的理論不外乎是商品形式的理論,因為這種規(guī)定貫穿了整體經濟生活,這個說法基本是正確的。但若要說由資本所產生的經濟邏輯是基于“商品化的假定”而被嚴格地推理出來的,則十分錯誤。畢竟,從商品形式“開始接管”經濟生活一直到“商品化程度”的完全化,這是個歷史關系的漸進生長過程,從而,邏輯的東西始終是歷史的東西,醞釀階級關系的邏輯不具有自我推理性。以價值規(guī)律為例,它實際上不是任何的推理,而是對商品生產規(guī)律和它的交換規(guī)律(即“貨幣流通規(guī)律”)的一種知識綜合,是對“商品生產方式的規(guī)律”的客觀陳述。表3中,價值規(guī)律的經是“商品生產方式的規(guī)律形式(總形式)”,價值規(guī)律的緯則是“生產一般I”(價值形式一般總論)。可見,“‘經濟規(guī)律’不能脫離歷史生產規(guī)律本體。”結論是,“從歷史內容看,價值規(guī)律屬于商品生產方式的‘內在規(guī)律’”,以至于“價值規(guī)律在完整意義上是按商品所有權生產和交換的統(tǒng)一,即作為了商品的歷史生產規(guī)律與其經濟運動形式的規(guī)定的統(tǒng)一……并且依照這個觀點,‘商品生產所有權規(guī)律’毋寧說是價值規(guī)律本身的范疇形式。”[6]
【[6] 許光偉.《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一[J].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4):29-42.】
![]()
(四)
同樣的情形適合于馬克思對資本積累一般規(guī)律的說明:這其實是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形態(tài)社會的一個總象意義的圖景描繪,即決定該經濟形態(tài)歷史發(fā)展趨勢的“總規(guī)律”;從資本主義生產規(guī)律的歷史形成到資本主義生產規(guī)律向資本主義流通規(guī)律的轉化,從資本主義再生產規(guī)律的社會形成到資本主義流通向分配的轉化,最終促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征性規(guī)律”的形成,——并且在這里,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規(guī)律成為統(tǒng)一它們的“總形式”。這是馬克思最終決定以“資本積累”為《資本論》全部主題最初總結的根由。然則,“以《資本論》而論,如上指出,設若《資本的生產過程》和《資本的流通過程》為‘合卷體’,那么,資本積累、市場、危機這三個范疇的寫作就會是另外一種布局,或寧可說目前的版本乃是原有底稿的‘重新布局’……一是資本的簡單再生產及其轉向規(guī)模擴大的再生產形式的研究……二是結合資本積累過程的危機階段機理的解剖……以說明資本積累兩種基本形式的動態(tài)回環(huán)過程……(可見)上述三個范疇的寫作內容,只不過是作為了資本主義全部本質研究的總結。”[4]
【[4] 許光偉.《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4):36-57.】
統(tǒng)之則治之,所謂錢而統(tǒng)之、分而治之。然則,“理論與實踐不是相互孤立的工作領域”,雖然在知識形制上,理論的自我結構化邏輯和實踐的歷史路徑彼此相對區(qū)隔,但由于堅持“經緯合一”,“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展開——從資本的生產過程到流通過程、再到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形式”,最終在價值形式“知”“行”的重新統(tǒng)一中,“實現(xiàn)了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事的意蘊的生長,從中定格階級的社會生產對象、流通對象、分配對象乃至認識對象。”
可見,表3引入《資本論》第四卷的方式在于肯定“《資本論》實際是從歷史部分和理論部分的統(tǒng)一開始。”[6]
【[6] 許光偉.《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一[J].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4):2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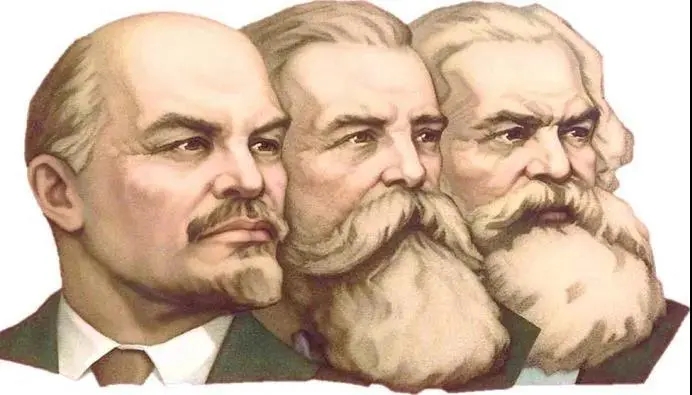
(五)
研究對象是行的基礎上的唯物史觀知識命題。
常見的誤讀是:它是不同歷史層級或對象范圍的“規(guī)律知識”的意義組合,這些知識在內容上彼此獨立、互斥,甚至混雜無序,只是依靠邏輯法則的強制或某種特別的綜合方法,它們才結成統(tǒng)一的工作整體。殊不知,《資本論》中各種規(guī)律并非“孤島的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的同一經濟形態(tài)規(guī)律的不同方面規(guī)定,可見,強調真理即規(guī)律之統(tǒng)一,并源自歷史本身,是多么重要啊!在歷史領域內,強調“知”“行”合一,猶言實踐與理論之統(tǒng)一。
所謂“知”“行”不二,則繼而指示知識生產的理論部分(邏輯)、歷史部分(歷史)統(tǒng)一,猶言研究與敘述之統(tǒng)一。知行合一歸根結底決定知行不二,如《資本論》首篇設計即是具體的體現(xiàn),是故商品生產方式的知識范疇必然是“商品和貨幣”。“價值形式轉化”是認識產物,也是實踐形式:道路規(guī)定是“交換過程”,系統(tǒng)規(guī)定是“貨幣=商品流通”;階級與拜物教的知識二重化運動自此萌發(fā),復由此展開。政治經濟學批判突出了真假學的重要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生命力在于其本質規(guī)定性的形成,即總公式II領導生產一般II的歷史規(guī)定性形成及其向總公式III領導生產一般III歷史規(guī)定性的轉化,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真的規(guī)定”;相較而言,資本主義藉以階級與拜物教統(tǒng)治之各種收入的形成乃“假的規(guī)定”⑩。
【⑩ 沒有對價值形式“真假同體”性質的揭示,就不能從知識生產上完成對“真假共相”的認識澄清。GDP(資產階級理論工作者對“各種收入”的命名)從統(tǒng)計實踐看,必然是真(價值計量)和假(價格計量)逐漸化合的經濟數(shù)值。從真假同體最終演變?yōu)檎婕俟蚕啵粍t,這是資本主義生產在外表上偽裝起來的經濟形式的知識形態(tài)學。】
理論上的緣由似乎是“利潤率取向下降的規(guī)律”(剩余價值分配的一般規(guī)定)使然,而“事實上,在資本理論的深層結構動力學中,生產的所有輸入和輸出必須完全商品化。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就沒有商品經濟的邏輯,資本也就不能作為自行增殖被概念化,同樣,經濟也不能清楚地從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中區(qū)分開來。”[2]29
【[2]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征性規(guī)律”的出現(xiàn)決非偶然,它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矛盾的社會產物,進一步是“以流通為中心的資本再生產運動”歷史生成規(guī)定的運動結晶。以價值形式統(tǒng)轄資本,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權力乃至權力、權威、權利之間的關系得到很好厘清,而有完整的資本生死歷程的生活呈現(xiàn)。資本形式的職能形態(tài)全面轉向“非職能形態(tài)”則表明資本主義統(tǒng)治方式的轉型升級達到了峰值水準,這是一個“死亡區(qū)間”,其必然導致“數(shù)量(計量)經濟學的極大崛起”,這種“形式化的牢籠”使人忽略乃至忘記資本的權力結構,直至將其剝削屬性和它可能帶來的生產效率直接等同起來。
那種把商品混同于產品,又把根植于交易過程的商品看成是完全的自然進化過程的人們最終試圖否認:“商品形式在歷史上(包括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經濟生活的,但是它在資本主義中是至關重要的,正是商品形式恰恰使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有了其獨特的性質,結果也表明了它是現(xiàn)代社會的核心。”[2]41
【[2]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未完待續(xù))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