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社會知識狀況考察之二
![]()
【總按語】對階級的考察自然離不開社會形態。但馬克思《資本論》鎖定的是“商品社會的經濟形態”,這就是價值的階級范疇和經濟的市民社會范疇。經濟的社會形態可以說是階級的動員令、廣告詞和集結號!《資本論》是關于階級的“理論寫實”,這樣有了《階級》的結束詞(第三卷第五十二章)。盡管馬克思沒有完成它,似乎是預留“實踐的沉默”,但業已留下階級工作辯證法。“首先要解答的一個問題是:什么事情形成階級?這個問題自然會由另外一個問題的解答而得到解答:什么事情使雇傭工人、資本家、土地所有者成為社會三大階級?”這個提問似乎重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工作場景。為此,馬克思必然需要解決“價值形式的時空穿越”問題。一言以蔽之,價值形式必然成為生產形式、階級形式、經濟形式的三者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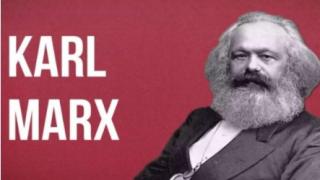
——本文系《<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的理論續作

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 - 烏有之鄉
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ichao/2019/12/411731.html
周建軍 肖嘯越丨基于Citespace的“資本論”期刊文獻知識圖譜研究
mp.weixin.qq.com/s/pF8HSoHLfj6lRcaeY0STuQ

接續上一篇:階級社會知識狀況考察之一-烏有之鄉
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12&id=448195&actid=02105
第二部分
如何把握“范疇法”:知行合一與《資本論》體系之成
——自古陽謀難解,可見,“范疇法”是階級斗爭不可逾越的知識階梯!
——那么,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范疇呢?
![]()
(一)
“在第一篇關于生產一般和第二篇第一部分關于交換價值一般中,應當包括哪些規定,這只有在全部闡述結束時并且作為全部闡述的結果才能顯示出來。”[3]280-281【[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如何理解《資本論》對商品的范疇規定,涉及唯物辯證法的意義解析,即“《資本論》必須視為唯物辯證法考古意義上的‘活化石’,是唯物辯證法完結形態的譜系。”[4]【[4] 許光偉.《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4):36-57.】
商品范疇起因于“異化問題”,由生產形態史轉向商品形態史的問題域而來,可見所謂抽象力,在于尋求“唯物辯證法定義”。道路經之,系統緯之;在唯物史觀領域內,抽象力規定直接表現為“知行合一”,從呈現形態看,又在于尋求“知行合一式的定義”,——所謂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商品工作范疇法即充分彰顯這一點。初言道路的知,次言系統的行,復言道路的行,再復言系統的知。在規定性上,道路蘊涵偏于“經之”(言統治路徑的“母子”),系統蘊涵偏于“緯之”(言統治階級之于被統治階級結構上的“體用”);其是對陰陽五行“偉大思維學工具”的創造性化用。這一構造即:知(道路)-行(系統)-行(道路)-知(系統),在于實現“知”和“行”的規定統一,從而,經緯合一的唯物辯證法方式又在于使“母子體用”定格為歷史之思維結構,乃至在藝術性上渾然一體。以《商品》前兩節內容為例:它對于唯物史觀范疇的明確是知與行,亦是經與緯的方式,——所謂商品生產的“歷史生產力類型”在于確立具體有用的勞動生產力“行的規定”和商品使用價值“知的規定”;同樣,所謂商品生產的“歷史生產關系類型”在于確立抽象的人類勞動“行的規定”和商品價值“知的規定”。然則在內容上,第一節的規定延伸是“道路之行”,而有了知的比類的歷史“行的具象”,第二節的規定延伸是“系統之知”,而有了行的綜合的歷史“知的具象”。于是經由歷史的知、行統一,商品世界的唯物史觀規定得以向價值形式結構轉化。

(二)
以“商品有機構成”為例,是形成了這樣的知識具象路徑:
有機構成I:商品的對象性存在‖勞動過程。商品對象正是從與勞動過程“歷史照面”中自身析出“使用價值”和“價值”。
有機構成II:商品生產關系‖勞動過程。在使用價值、價值兩個對立統一的因素基礎上,商品生產關系通過與勞動過程“社會照面”進而從商品生產方式中析出“商品生產勞動”。這樣所謂由商品所體現的“勞動的二重性”,實則指示和W(L)直接有關的三個工作范疇:使用價值、價值、商品生產勞動。
有機構成III:商品交換關系‖勞動過程。研究對象基于歷史對象而成,如上指出,商品社會研究對象的行動規定正是價值形式;從而在商品生產勞動的二重性質基礎上,在商品生產關系通向交換關系的意義域中必然進一步析出“價值形式”。
有機構成IV:商品生產方式‖勞動過程。對象→價值形式→研究對象,這正是知行合一的工作路線;在交換價值發展(道路形態的價值形式)基礎上,再以商品生產方式從意識形態行為中析出“商品拜物教”,由此形成有關于W(L)的生產一般。

以上過程具象為5個術語組成:商品生產勞動、使用價值、價值、交換價值以及商品拜物教意識,以后引出剩余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資本積累以及本身以貨幣拜物教意識為導引的資本物格崇拜的生產方式意識(即資本拜物教及其市場拜物教意識形式),——后者是指涉m(L)的生產一般。這種“商品生產一般”作為商品生產方式的基本理論,必定與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理論的“資本的生產一般”內在契合,它們的生長秩序必定是嚴格對應,并且按照統一的知識形制來設置。故其正是價值形式所支持的一般知識,乃至是與總公式“知行互譯”的實踐知識②。
【② 所謂:“考慮到有關深層理論的重要性和商品形式的廣泛性,勾勒出商品的一些基本特征是非常有用的。商品,首先它是一個東西(實際上是私有財產的一部分),可以賣出或買入,作為一個單元,它是一種私有財產權力的社會關系……是一種私有財產的形式,商品形式給資本家的占有權提供了巨大的結構力量。”(參見《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第30-31頁,新華出版社2013年出版)】
行是統一的,知必然統一。歸根結底,價值形式是在“有機構成的歷史”“有機構成的矛盾”“有機構成的規律”“有機構成的范疇”乃至“有機構成的概念”意義上運用的中介工具,“歷史→矛盾→規律→范疇→概念”并非辯證推理,而是知與行的辯證結合,旨在將階級、研究對象、政治經濟學批判落實為唯物史觀的內部工作規定③。

【③ 相比W(L)形式,O(L)即共同體生產。無獨有偶,如果我們將商品構成對生產一般術語的生產轉換成共同體構成的場合,結果也是一樣:(1)有機構成I:共同體‖勞動過程,從共同體對象中析出“分工”和“協作”。(2)有機構成II:共同體生產關系‖勞動過程,在上述兩個對立統一因素基礎上,在共同體生產關系中繼而析出“共同體生產勞動”。所謂由共同體所體現的勞動的二重性,同樣指示了三個工作范疇:分工、協作、共同體生產勞動。(3)有機構成III:共同體交往關系‖勞動過程,從共同體生產勞動的二重性質的基礎上,在共同體交往關系中進一步析出“協作形式”。(4)有機構成IV:共同體生產方式‖勞動過程,在協作形式發展基礎上,通過落腳于“歷史生產方式的意識”,最終形成“O(L)的生產一般”。在知識圖像上,其同樣具象為5個術語組成:共同體生產勞動、分工、協作、協作形式以及共同體人格崇拜的生產方式意識,以配合于統一的行動規定——主體關系形式。】

(三)
所謂根本,即呈現事物生長方式的道路和系統,包括道路類型(如生產和再生產)、系統類型(如統治方式)和道路結構(如唯物史觀結構因素)、系統結構(如矛盾)以及道路形態、系統形態;所謂抓住根本,是抓住道路和系統內在聯系——這同時是實現對事物生長方式“歷史認識”的規定(如有機構成范疇),知行合一成為“根本”則是使唯物史觀的這個實質規定進一步落實為實體與工具的統一。《資本論》從道路出發,從歷史道路的類型和結構出發,就深層次觸及了“階級檔案學”;因此必須肯定,“對于《資本論》來說,開篇是作為‘通史’加以考察的。”[5]【[5] 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5):5-31.】
它指出,“道路的以太同時也是‘系統以太’,規定著實體與形式的轉化”,而“一旦某種階級關系及其思想類型在系統中占到一定比重關系,便發生總公式的形式裂變。”[6]【[6] 許光偉.《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一[J].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4):29-42.】
這樣可概括完整的《資本論》“價值形式意義”:階級關系類型(道路類型和系統類型)→階級關系結構(道路結構和系統結構)→研究對象→階級關系形態(道路形態和系統形態)→有機構成的歷史知識具象(道路-系統的內涵和外延);然道路和系統分殊乃是相對之狀態,比如:一方面對生產關系而言,生產方式是“道路”,對交換關系而言,生產關系則是“道路”;另一方面,言生產關系是“系統”,指示階級關系意義的統治方式的類型形成,而言交換關系是“系統”,乃指示拜物教統治的社會結構化形式的進一步系統形成。馬克思從中提煉出“道路-系統”的社會歷史結合,言知行說到底是道路-系統工具;知行合一是形成認識的根本所系,“因此,廣義的抽象力一定也是指人類思維的總體規定性,即總體學科的‘行-知’路線圖。”遂達成工作效果:“以‘實踐化的知識’切入行動理論,確立研究規范與敘述規范工作運用狀態的統一,為統一之歷史科學宏基。”[7]【[7] 許光偉,許明皖.馬克思“抽象力”理論規定本根與溯源——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J].中國經濟問題,2018,(4):12-25.】
這促成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的徹底解決,亦說明“道名”的拆開即“道路-系統”與“知行”問題,但理論上的真正解決委實在《資本論》中。

(四)
《資本論》原理的意義在于實現歷史唯物主義與階級(斗爭)原理的合而為一,不僅《商品》前兩節,而且全部四節內容都是一個工作整體:前兩節實現的是唯物史觀范疇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知識具象,后兩節實現的是階級關系范疇即階級和拜物教的知識具象;然則,“作為總論,《商品》邏輯是對《資本論》四卷體式尤其理論部分的工作錨定……從總體上看,四卷體式毋寧說是對《商品》的一種邏輯上的擴展和應用形態上的實現,疊合二者的工作線索恰好就是階級關系內涵的有機構成。”[5]【[5] 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5):5-31.】
這揭示了階級-拜物教的“知”和“行”,它的根據是有機構成世界,它的具象場域是價值形式世界,如果僅僅將價值形式理解為知,則“《資本論》資本主義社會表現出來的仿佛是一個巨大的形式系統——資本形式化系統,并且這些形式化的規定仿佛就是商品形式的若干邏輯學的‘操作’。”[4]【[4] 許光偉.《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4):36-57.】
《資本論》當然不是形式化的知的系統,所謂“形式化”,僅僅是拜物教的統治工具,又利用“1=1”的價值理性進行了數學偽裝。其得以仿真的根據是“只有在純粹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背景下才可以運用數學公式,在這種純粹的社會里,權力關系完全被融合進社會經濟結構,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又完全歸入商品形式中,這樣,數學公式才能被運用”,說到底,“以資本為例,商品化意味著一種社會關系的自我客體化。”[2]11【[2] 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但是,“把馬克思的分析局限在資本主義一般的層次上(如系統辯證法那樣)或現代資本主義的層次上(如關注‘全球化’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和所有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那樣),就把我們為了既認識世界又改造世界所需要知道的東西足足排除了一半……如果忽略了從其起源的角度來考察事物可以獲得的認識,我們也就不能全面地理解任何結果——以及什么不是某物的一個結果……《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僅力圖表明資本主義是如何運行的,而且力圖表明它為什么是一種過渡的生產方式,繼之而來的可能是什么性質的社會,以及如何使這么巨大的變化得以發生。所有這些都包含在他關于資本主義如何運行的辯證分析之中。”[8]【[8] 奧爾曼.辯證法的舞蹈——馬克思方法的步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246-248.】
“雖然馬克思的理論是在將商品形式掏空后而發展起來的資本理論,但隨著理論的展開,這個最基本的要素發展起來的理論開始成為完全資本主義的商品形式”,換言之,它表明:“資本邏輯的內在邏輯是商品形式作為一種商品經濟邏輯已完全化,并成為一種霸權。”[2]47-48【[2] 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商品形式何以能夠被看作合乎邏輯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全面的規定”,在于價值形式統治秩序建立的自然歷史過程。然則,它必須同時被理解為行,即價值關系的行動規定。價值形式不限于作為商品價值或社會價值關系的表現形式或方式、運動形式或形態,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價值之行”規定性。價值形式是圍繞價值關系的經濟運軸,是價值關系在結構、形態上的轉換或轉化的生成運動,是自我構造化的過程和運動系統。如在研究對象這個問題上:價值形式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行(如階級統治道路:貨幣轉化為資本),它的知是資本主義統治方式的歷史類型知識(如簡單勞動→雇傭勞動、價值→剩余價值、商人總公式→資本總公式);價值形式同樣屬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行(如階級統治類型:勞動力成為商品),它的知是資本主義統治方式的歷史結構知識(如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計時工資→計件工資、資本→資本積累);價值形式同樣屬于資本主義交換關系的行(如作為階級統治的資本積累系統),它的知是資本主義統治方式的歷史形態知識(如產業資本→職能資本→非職能資本的交換價值)。《資本論》研究對象具有統一的名——財產關系的價值形式,它作為行的規定:既是直接生產過程,也是流通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還是分配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是統一形態的“階級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④。
【④ 唯物史觀知識命題定格研究對象表達。這種表達集中于經濟的社會形態范疇,專注于質與量統一的如何社會實現,而不屈從于一般的科學邏輯。它通過研判“階級史觀”獲得對權力結構的完整理解,致使歷史與經濟不同層面的考察以極為合理的方式被組合。然則,這一路線意味著“唯物史觀知識”貫徹在對象的全部領域中的實現,造成對歷史典型事實的需求。以至于《資本論》英文版對研究對象的處理,更多采用學科類型比較視角的社會形態結構學的定義方式,所謂:The physicist either observes physical phenomena where they occur in their most typical form and most free from disturbing influence, or, wherever possible, he makes experiments under conditions that assure the occurrence of the phenomenon in its normality. In this work I have to examin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corresponding to that mode. Up to the present time, their classic ground is Engl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England is used as the chief illust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y theoretical ideas. 】
《資本論》之所以邏輯體例完美,又在于從資本主義階級統治道路的源起說起(資本之社會形態“生”),從一個剝削關系的特殊的典型的類型和形態上展示階級統治的結構化系統,繼而證明它的歷史衰敗性(資本之社會形態“死”),是為資本與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檔案學的“復調合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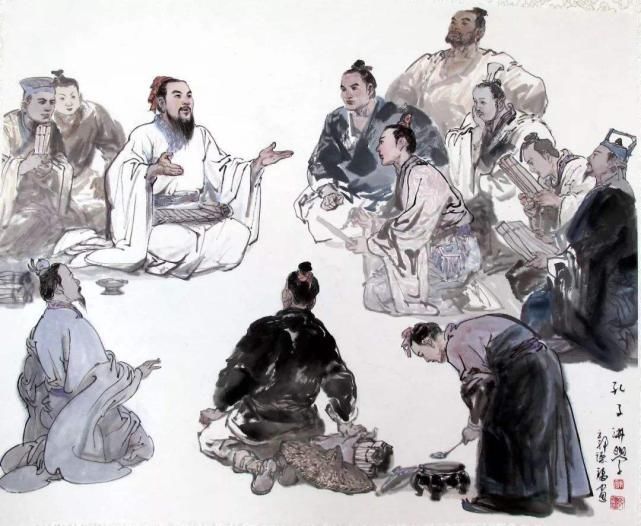
(五)
歷史者道路與系統也,邏輯者知與行也,邏輯與歷史一致者工具的歷史唯物主義指向也。是以道路為知,系統則為行;反之,道路為行,系統則為知,如此成就以道路、系統為依托的知行合一。對研究過程來說,是從歷史和實踐中取出“道路”“系統”,乃至建立“對象第一性”“研究對象第二性”;顯然,這是《資本論》基礎的第一步工作。對敘述過程來說,則是從知行合一出發,將知行合一的“行”(即歷史學家的生產關系)繼而展開為知行合一的“知”(即經濟學家的“行”和“知”);顯然,這是《資本論》接續的第二步工作。相較而言,對象偏重行,研究對象偏重知;乃至對象和研究對象結合起來則成為:對象是行(有機構成世界)→知(生產關系),研究對象是行(價值形式世界)→知(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正是以生產關系為中介——生產關系從“知”(唯物史觀的知)到“行”(階級斗爭的行),研究對象復又成為“行→知”認知結構。簡單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生產關系的行”是同和異的統一:從通史方向看,這正是資本歷史道路之行之知與資本社會系統之行之知的邏輯結合之處,于是有更為巨大的唯物史觀工作規定性,可從中提取階級生產方式形成和建立統治結構的“知行合一范疇”。這給了統一的價值形式“行的規定”存在的理由。價值形式不是邏輯的意志,不限于對自我結構表現的社會形式的認知,更為重要的是作為行動的意志,最終成為階級結構化統治的生成方式和統一表現形式。

參考文獻
[1] 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1):5-22.
[2] 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許光偉.《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4):36-57.
[5] 許光偉.有機構成、人的發展與黨的策略問題——通史道路的理解域[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5):5-31.
[6] 許光偉.《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一[J].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4):29-42.
[7] 許光偉,許明皖.馬克思“抽象力”理論規定本根與溯源——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J].中國經濟問題,2018,(4):12-25.
[8] 奧爾曼.辯證法的舞蹈——馬克思方法的步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246-248.
[9]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11] 許光偉.論生產一般的思維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啟示[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1):5-18.
[1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 仰海峰.《資本論》的哲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155-156.
[14] 許光偉.勞動過程與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貢獻的性質[J].當代經濟研究,2020,(4):11-23.
[15] 許光偉.生產關系的三層次解讀關系及其意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域內的道名學說和生長論[J].當代經濟研究,2016,(10):5-13.
[16] 張開.試論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生產形式”[J].經濟縱橫,2020,(8):1-8.
[17] 許光偉,胡璇.工資的身份形式與財產形式理論問題研究——兼議中國共產黨的按勞分配觀[J].當代經濟研究,2021,(9):5-16.
[18] 許光偉.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品性與理論品格——基于《資本論》的視角[J].經濟縱橫,2018,(3):12-24.
[19] 許光偉.論生產目的規定的抽象性與具體性理性——中國共產黨對經濟學“哥德巴赫猜想之謎”實踐解決的理論內涵和意義[J].內蒙古社會科學,2021,(6):105-113.

轉自昆侖策:?階級社會經濟形態知識狀況考察
mp.weixin.qq.com/s/fQxYP2JJnAd6ZE4jeaXUbA
(未完待續)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