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雖然其中的“禁止PUA婦女”等條款因為對大眾來說概念不清而受到一定爭議,但也有不少與時俱進的改進,尤為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條: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前段時間那篇引起巨大爭議的《“暖大齡男被窩工程”很有必要》。
文章提出“目前農村大齡青年擇偶難問題比較普遍和突出,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婚姻問題正在逐步由個人問題轉化為社會問題”,但給出的解決方案卻令人頗感意外:要“鼓勵女青年留在家鄉”,解決大齡未婚男性“暖被窩”的困難。

這個離譜到讓人感覺有點“高級黑”的說法,其實是有著社會根源的。如今城鄉的女性權益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東西。
問題的本質,在農村的土地制度上。
農村女性土地權益難以得到切實保障。
畢竟土地是農民生存生活的基本要求,也是現代國家必須妥善解決的基礎性問題。土地權益受到侵害,就相當于斷了農村女性謀生的重要后路。
1
烏鴉之前講到過,真正科學的性別平權,必須基于對婦女勞動權益和勞動能力的保障。
其實這一點我們有很好的基礎。相比于多數發達國家共產黨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城市女工權益,中國共產黨是最早認識到農村女性土地權益重要性,也是最早和最成功賦予農村女性土地產權的現代政黨。
從解放區男女平等的土地政策到新中國初期的“平分土地”,再到合作化時期的“集體公有制”,以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二權分置”和“三權分置”,對農村勞動權益基礎的土地制度格外關注。

建國初,國家政策就提出要在土地證書上寫女性的名字,打破了貫穿中國上千年的以戶、丁為準進行土地屬權和勞動權分配的體系,在農村土地公有制的條件下,女性對土地的所有權是很自然的事。
當然制度設計需要執行的保障,此后的歲月中相關法律法規也在建立健全之中。
1992年制定并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對土地權利做出了明確規定。該法第三十條規定,“農村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批準宅基地,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不得侵害婦女的合法權利”。“婦女結婚離婚后,其責任田、口糧田、宅基地等,應當受到保障”。
這是第一個對農村婦女土地權利做出專門規定的法律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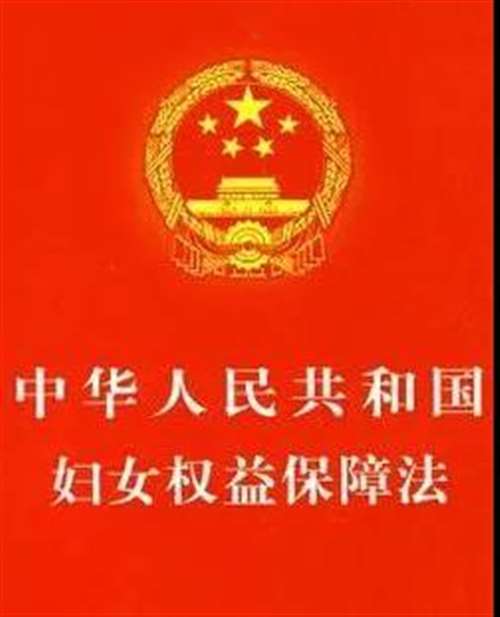
除此之外,在繼承法、民法通則等有關法律中有類似的保護婦女土地權利的法律原則。
2001年5月8日發布的《關于切實維護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益的通知》,第一次比較完整、系統地頒布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的具體政策措施。
該通知規定了在農村土地承包中必須堅持男女平等,出嫁女性必須有一份承包土地,離婚或喪偶女性在土地承包權問題上不受歧視,并要求法院對相關侵權案件依法受理、及時處理。
但在所有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很多新的農村家庭中,出現了家庭成員財產關系不明晰的狀況,土地管理法、承包法,都未強調將夫妻雙方的名字記入土地經營權證書。在農村就突出體現在女性土地權益的歸屬并不完全屬于自己。這就導致,女性以戶籍為根據獲取的土地并沒有法律上的憑證。

農村現行土地所有制度,以戶為單位,可以說“戶主”擁有較大權利,事實上成為家庭生產經營和利益分配的決策者,是家庭在社區中的代表,負責代表全家參與社會活動,甚至可以“準法人”的身份活躍于市場。
而在“戶主”這一層面,農村女性確實在事實上處于弱勢地位。
而且一旦女性因離婚、喪偶后再婚等原因與原來的丈夫家脫離,就很難保障自身在原來這個家庭的各項合法權益,畢竟分配權不掌握在女性自身、而是掌握在戶主手中。
由于不掌握分配權,事實上的侵權。
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無地農村婦女占21%,比過去有所增加。農村女性在國家政策支持下所進行的維權行動時有發生。2016—2017年,全國婦聯收到婦女土地權益相關投訴共計8807條,比2014—2015年增加了182%。
2
2019年底,農村婦女安琪通過訴訟擺脫了家暴出軌的丈夫,以及束縛了她10年的婚姻。
第二年3月,當她想把戶口從前夫家遷回自己的老家,卻被律師告知,光有離婚判決書還不夠,要先向法院申請判決生效證明,再辦理戶口遷入地——也就是老家的準予遷入證明(準遷證),才能去目前的戶籍所在地辦理遷戶手續。

安琪提供的娘家村準遷證
好不容易把兩份證明拿到手,安琪又要面臨兩個新問題:戶籍地的派出所要求她必須自己向村委索要戶口本,如果村委拒絕提供,再去找派出所出具證明。盡管正值疫情,遷戶手續還是必須由本人現場辦理。往返都要面臨9天的隔離期,而安琪最長只能向工廠申請14天的事假,時間根本不夠,只能選擇辭職。
安琪在電話里和派出所反復溝通無果,無奈決定還是要跑一趟。且準予遷入證明的有效期是40天,等到發薪日已經超出了時效,她必須再一次申請,重走一遍流程。
遷戶口能不能成,還取決于娘家村同不同意。
幸好,盡管經歷了種種繁瑣的程序,她還是在短時間內幸運地順利辦下準遷證。更多像她一樣的女性卡在了這一環,被生養自己的村莊拒之門外。
這就使得離婚的農村女性一旦離開了婆家村,又不被娘家村所接納,境遇就會一言難盡。
安琪,其實就是土地權益受侵害的農村女性的縮影。
這樣的問題,當然有一些糟粕傳統的影響,但問題又不是如此簡單。

傳統觀念中的男“娶進”、女“嫁出”,就意味著女性結婚后一般都是到男方家落戶和居住,即所謂的“從夫居”,這在絕大多數人心目中都是約定俗成的。
更從經濟的角度,在分享村莊集體所共有的資源和利益的問題上,女性遲早會因為結婚而離開父母和生育養育她的村莊,都是暫時的流動成員,不僅不能對所在家庭和村中的發展及福利做出永久性貢獻,還會將家庭和村莊投入到她們身上的資源轉移到丈夫家里和丈夫所在的村莊。
這就導致,女性在接受父母的關照和教育等方面,所接受的投資往往小于同等條件的自家兄弟。在事關重大的耕地方面就更是如此。
當前,很多村莊隔幾年會對承包土地進行調整,這就意味著有的農戶家庭隔幾年就有可能失去部分承包耕地。
而在具體調整過程中,首先失去土地的往往是那些待嫁女、出嫁女、離婚和喪偶婦女。
很多村莊在“土地資源稀缺”這一根本限制下,盡可能排斥“非集體成員”擁有土地。在他們看來,在30年不變的長期限規定下,此期限內待嫁閨中的姑娘們都是潛在的非社區成員。

畢竟“從夫居”意味著出嫁女的戶籍將從娘家村遷移到婆家村,而戶籍人口是決定農村耕地多寡的最主要依據,這就意味著農村女性會因為結婚而喪失娘家村的耕地承包和利用權,也就是農村女性因為結婚而面臨的第一次財產損失。
有的村莊以“測婚測嫁”為依據,對未婚女性不分或者少分土地。
嫁入婆家村的新媳婦可能得不到承包耕地,畢竟大部分村莊沒有足夠的機動承包耕地,導致分耕地還需要“排期”。
部分農村女性結婚后將戶口遷至婆家村,因此喪失娘家村的耕地,盡管本人乃至孩子可能還在娘家村事實居住,仍面臨在實際居住地無耕地可依的現實,就會失去重要的經濟來源。
而離婚或者喪偶的農村女性,又可能在土地權利方面面臨一次損失。

離婚又離村的婦女,因其戶籍的變化,承包土地可能被所在村莊集體收回,或者由離異的丈夫家庭繼續承包和使用。
有的村莊強行注銷出嫁女、離婚或者喪偶婦女的戶口,從而收回土地。
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土地被看成夫家的財產,離婚婦女不敢提出要土地的要求,由于怕失去土地而失去生活來源,所以有些婚姻關系已經破碎的女方也不敢輕易言離婚。有的村莊因無土地可用于分配,不接收離婚婦女的戶口,導致離婚后的農村女性既無法將戶口轉移回娘家村,也長期無法獲得承包耕地。

在婚姻關系的變化中,也有很多農村女性不自覺地放棄了屬于自己的那部分合法權益。她們中的許多人甘愿或被迫在出嫁或離婚后將屬于自己的一份土地留給父兄、前夫或前夫的家庭。
無論是“兩邊無地”、“娘家有地”、“夫家有地”還是“人地分離”,都可能因為農村女性實際居住地和婚姻狀況的變動而帶來土地權益的受損。
在土地為根本的農村,徹底失去土地權益的婦女,面臨的處境堪比無家可歸。
3
如果家庭婚姻關系穩定,土地權益歸戶主和其他家庭成員共同共有,農村女性的土地權益,在家庭庇護下是相對穩定而有保障的。
但一旦婚姻關系發生變化,分配到“戶”的土地權益原先由戶主二次分配,現在需要明確到每一個家庭成員,農村女性的土地權益問題就會充分暴露出來,常常集中表現為土地糾紛。
面對這種土地糾紛,權益受損的農村女性該怎么解決呢?

要么出于對與前夫家的感情和照顧子女的需要,選擇離婚不離家、也不將戶口遷出,從而事實享有對原有土地的使用權。
要么想要維權,卻出于對原婆家村“村規”的懼怕,或出于對原夫家的恐懼,加之返回娘家村之后,發現原有的耕地因出嫁被收回,被迫放棄應由自己獲得的土地權益,導致無耕地可依。
要么選擇強勢維權,積極通過合理渠道申訴和保障自身權益。
但可依靠的渠道,十分有限。
這,也成了越來越多農村女性不愿意結婚的重要原因,換句話說農村的“結婚難”很大程度上是來源于“離婚難”。這跟城市的“結婚難”問題大不相同。

當然,面對農村生產力有限、收入不高的現實,也有更多農村女性選擇外出務工,相對的也就有了很多農村男性留守,這就是前面所說到那篇文章中“缺暖被窩的農村女性”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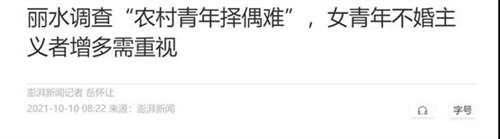
相比于城市的婚姻問題和女性權益問題,農村的同類問題,要清晰得多。當前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政策層面也在提出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案。
除了開篇說到的《婦女權益保障法》與時俱進進行修訂外,去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陳中紅就高度重視農村女性土地權益保障問題,提出應通過多種手段逐步解決農村婦女因出嫁、離婚等喪失土地權益保障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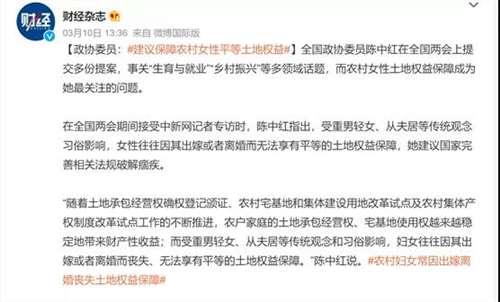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自治法》也在修訂完善中,將自治法的執行情況列入年度重點監督項目,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該法律或對該法相關條款進行立法解釋,減少各個村鎮通過自行解釋法條不平等分配權益的情況發生。
畢竟,農村土地權益,也就是勞動權益,如果不能切實保障勞動權的平等,談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呢?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