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為第二篇,主要講述改革開放之后勞務派遣制度的發展狀況。
文 / 林少貓
03.
狂涌
① 國企改革→派遣和外包
改革開放以來,原有的以固定工為主體的城鎮用工制度被廢除,勞動合同制作為主體的用工制度在全國推行開來。與這一轉換齊頭并進的是派遣工和外包工從計劃年代的暗流,奔騰成狂涌。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人口的普遍增加和知青的大量回城,城鎮就業壓力巨大。為此,中央政府鼓勵地方政府建立勞動服務公司。這類公司其實是之前勞動服務隊更加正規的形式。一時,地方上的勞動局、人事局、工會、街道和國企紛紛響應。1987年,全國有5.6萬家勞動服務公司,雇傭了730萬工人,并管理著170萬臨時工。勞動服務公司的服務對象是失業半失業人員和國企改革中的冗員。公司為他們提供培訓、介紹工作,或將他們派遣到用工單位去勞動,或將他們組成服務隊承攬工作。
新時期的派遣工和外包工最初是國企改革的伴生物。一旦一個工人被確定為冗員,這個工人一方面在勞動關系上與國企保持不變,另一方面被歸入國企附屬的勞動服務公司管理,其中相當一部分被派遣或外包到外單位。通過派遣和外包,原單位不僅減少了冗員,還能坐收外單位的傭金。在上世紀90年代,隨著國企改革進入深水區,下崗職工越來越多,政府要求國企成立再就業中心,這些中心除了向下崗職工發放生活津貼和給他們支付勞動保險外,職能與80年代的勞動服務公司無異。這些中心在新世紀初期被陸續關閉。同時,為了幫助下崗職工再就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大力鼓勵勞務派遣公司的發展,并為此出臺了財政補助和稅收減免等措施。例如,1999年出臺的《北京市勞務派遣組織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新建勞務派遣組織招用下崗職工達到30人以上,并與其簽訂2年以上勞動合同且試用期滿的,可享受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及同級財政部門給予的5-20萬元的一次性補助……勞務派遣組織招用下崗職工,達到職工總數50%以上的,且勞動關系維持在3年以上(含)的,可自安置人數達到規定比例之日起3年內享受營業稅等額補助的優惠政策。2003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一次發言中指出:“我們要積極發展勞務派遣和其他類型的就業服務組織,指導分散單個的下崗失業人員組織起來,為他們實現再就業提供組織依托和幫助。”
對國企的工資總額管控也是其大量使用派遣工和外包工的原因。為了提升國企效益,1985年起,國企的工資總額與其經濟效益掛鉤。而根據國資委制訂的國企會計準則,只有正式工的工資計入工資總額,臨時工的工資計入營業費用,在國資委的管控之外。而且,國企正式工的收入常年高于社會平均水平,而臨時工的工資則低得多。由此大量雇傭臨時工不僅能幫國企降低用工成本和提升經濟效益,還能幫國企擴大工資總額,鞏固既得利益。
② 對外開放、城鄉遷移→派遣和外包
外資進入中國也助推了勞務派遣的發展。對于早期進入中國的外商駐華代表處和外資公司而言,他們對中國知之甚少,招工不便。同時,政府意圖通過控制用工來監管這些外國機構。我國最早的一家專業派遣機構——1979年成立的北京外企人力資源服務公司(FESCO)——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這類外資人力服務公司至今是中國勞務派遣市場上的一霸。之后雖然外資機構有了招工權,但是使用派遣工的做法長期維持下來。外資企業使用派遣工的另一個原因是:一些跨國企業總部對于其中國分公司的人員數有控制,使用派遣工可以繞過這種控制增加員工。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村放開。城鄉遷移的浪潮推動了勞務派遣的發展。雖然絕大多數農民工是自發或者在自己親朋好友的幫助下遷徙到城市工作的,但有的農民工在遷徙過程中得到了當地勞務派遣機構的幫助。這些機構的組織主體是縣和鄉鎮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地方政府也會協助將農民組成建筑包工隊或者保姆隊,對外承攬服務。這類實踐在今天仍然存在,特別是在一些偏遠落后地區。在去年結束的脫貧攻堅站中,政府對外輸出勞動力來幫助群眾脫貧是重要的做法。近期熱播劇《山海情》中白麥苗到福建打工的經歷就是對這種做法的熒幕呈現。

③ 勞動力密集產業→派遣
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也推動了勞務派遣的狂涌。例如,在上世紀80年代的東莞,為了滿足蓬勃發展的出口加工業的需求,當地政府不僅自己成立勞動中介為企業輸送人力,也鼓勵私人中介的發展。同一時間的溫州也見證了私人中介的崛起,為繁榮發展的私企提供人力。這些中介最早靠向求職者收錢營利。隨著用工荒時代的到來,他們轉向向用工企業收費營利,其主要形式就是勞務派遣。在用工荒時代,之前工廠在門口貼個招工告示就能引來求職者如過江之鯽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用工荒疊加新生代農民工短工化之下,工廠自行招人變得過于昂貴,從而不得不求助于勞動中介。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疲軟,中國出口受到影響。對于工廠經營者而言,以前不僅有足夠的工人,也有足夠的訂單;而現在,不僅工人難招,訂單也難找。這種情況意味著訂單的波動性變大。為了控制成本,企業必須同步實現勞動力的波動。這種情況是目前中國出口導向型工廠的常態。
勞動中介的作用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幫助工廠招募到足量的工人并合法解雇不需要的工人,特別是在訂單量劇烈波動、企業必須在短時間內大量擴增或削減人力的時候;合法解雇的需求在《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后變得尤為迫切;另一個是幫助工廠降低工人流動率。勞動中介能實現第一個作用主要是因為它們之間的合作關系往往形成一種層層分包的中介鏈條甚至網絡,這種鏈條和網絡能讓它們的觸角伸展到很多地方,接觸到很多工人。由于勞動中介掌握了勞動力的供給,它們不甘心只賺取一次性的招聘費,而是傾向于按照提供的勞動力的工作時間收取人頭費,比如100元每人每月。這時勞務中介就變成了勞務派遣公司。現實中,二者界限并不清楚,因此本文對兩個術語混合使用。勞動中介的第二個作用是第一個作用的延伸。對于工廠而言,招進來的工人流動率高是個大問題。工廠愿意接受每月向勞動中介付費的原因也在于此。這種按月付費將降低工人流動率變成勞動中介的問題。勞動中介往往通過派駐駐廠管理人員,向工人提供服務,調解工人和廠方的矛盾,來穩定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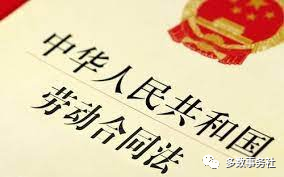
④ 《勞動合同法》→派遣
2008年1月1日,《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該法極大地加強了對正式工的法律保護。該法最重要的條款包括:(1)勞動合同訂立條款: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超過一年沒訂合同的,視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已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2)無固定期限合同條款:用人單位連續雇傭勞動者超過10年,或者連續第三次與勞動者訂立合同,應當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3)非法解雇賠償條款:非勞動者過錯,用人單位在合同到期前解除合同,應該向勞動者支付雙倍的經濟賠償金。這些條款加大了用人單位不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的風險。而一旦簽訂了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就失去了解雇員工的自由,因為必須考慮賠償。此外,2011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社會保險法》和2002年修訂的《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了用人單位在“五險一金”方面的義務。而五險一金加起來往往占到個人稅前工資的40%以上,成為用人單位欲逃之而后快的巨額支出。
為了逃避這些義務,企業大量使用派遣工。派遣工與勞務派遣機構簽訂勞動合同,再派到企業去上班。這樣勞務派遣機構成了用人單位,是上述各種義務的第一承擔者,企業只是用工單位。通過使用派遣工,用工單位在員工方面不僅能實現召之即來,也能通過隨時退工實現揮之即去。無固定期限條款和非法解雇賠償條款在派遣機構那里并不構成問題。當員工被退回派遣機構,派遣機構要擺脫他們就很簡單:只需把他們派遣到他們壓根不想去的工作崗位,就能迫使他們自動離職,這樣就達成0成本解雇的結果。至于五險一金,我國目前的執法力度并不大,正式工尚且存在不繳、漏繳、不按實際工資基數繳等情況,派遣工就更不用說。不少企業的做法是給少量員工繳納五險一金,以備檢查。
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派遣工大量擴張。關于我國派遣工的數量,沒有一致說法。其中較為權威的是全國總工會的估算:2011年,我國約有4200萬派遣工,其中企業3700萬(占企業職工總數的13.1%),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500萬;其中國企中16.2%的員工為派遣工,在電信、郵政、石化等一些央企中,派遣工更是占到了60%以上;港澳臺和外商投資企業中14%的員工為派遣工;2011年上海市調查所涉1805家企業的40多萬名職工中,勞務派遣工占25%,比2007 年增長了36.1%。
⑤ 從派遣到“外包”
面對派遣工的濫用,國家嘗試過通過立法加以限制,用工單位對此的回應是大量使用外包工。實際上,《勞動合同法》一開始就有一節關于勞務派遣的內容,規定了勞務派遣單位和用工單位各自的義務,但顯然這些規定沒有阻擋住派遣工的泛濫。2013年7月1日,《勞動合同法》的修訂案開始實施。這個修訂案提高了勞務派遣業務的準入條件,進一步明確了派遣工與用工單位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標準,也強化了對派遣工使用范圍的限制。
最嚴格的規制來自2014年3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勞務派遣暫行規定》。這個規定只限制企業,不限制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它要求企業在2016年3月1日前把派遣工在總員工數中的比例降到10%以下。這個規定的初衷是迫使企業把派遣工轉正。但是企業不愿意這么做,而是把派遣工大量改成“外包工”,以達到降比的目的。為了完成這個改造,企業只需和勞務派遣機構簽訂一份外包合同,勞務派遣機構以發包費(包括了派遣機構的服務費和派遣工的工資)為基數納稅即可;而這之前勞務派遣機構是以服務費為基數納稅的。在這個過程中,提供第三方服務的中介機構往往不變,工人也仍然是用工單位在管理,變動的只是文書和交稅方面而已。因此,這種做法被稱之為“真派遣、假外包”。它是企業降低派遣工比例的主要手段。實際上,外包業務門檻比派遣高得多,用工單位一方面在市場上找不到靠譜的外包機構,另一方面也不愿扶持起一個外包公司跟自己競爭。其結果必然是“真派遣、假外包”的泛濫。政府并非沒有預期到企業的這種應對手段。實際上,《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的征求意見稿曾指出:用人單位將業務發包給承包單位,但對從事該業務的承包單位勞動者的勞動過程直接進行管理的,屬于勞務派遣用工。但是這個條款在《勞務派遣暫行規定》正式頒布時被刪除了,使得企業可以有恃無恐地濫用“真派遣、假外包”來達到降比目的。
《勞務派遣暫行規定》之后,派遣工和外包工泛濫依舊,但是沒有新的規制措施出臺,而且舊措施的執行力度不高。實際上,隨著經濟增速下滑,勞動政策如何服務于企業降本增效的問題被推到了幕前。為了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廣東省等一些地方降低了企業的社會保險繳費比例。這種做法與企業通過勞務派遣逃避社保義務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勞務派遣規制執行的松弛度由此可想而知,實際上也處于一種民不舉官不究的狀態。根據筆者團隊2016年在廣州、深圳、天津、長沙等多地對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的調查,超過一半的員工都是派遣工是這類企業的普遍情況。/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