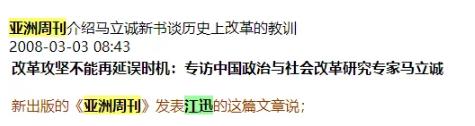香港資深媒體人、《亞洲周刊》副總編江迅突發心梗猝然離世了,享年74歲。
江迅一些好友在他離世以后開始痛斥香港的公立醫院:
據稱,江迅10日因發燒及抽搐進了仁濟醫院急癥室,第二天醫生稱無大礙,之后回家休息,晚上又再發作,家人急召救護車送院醫治。因為防疫要求,香港的公立醫院不許家人陪護,江迅只能用手機和家人聯絡,他告訴太太,“痛了叫了十幾廿個小時,一直沒人理他。”
大公文匯網的文章稱,“12小時后主診醫生才出現,劇痛超過24小時后離世,院方完全沒半句交代,醫生更無現身。”
畢竟“死者為大”,但這個事件認真計較起來卻多少有點諷刺。
香港的醫療體系延續了殖民地時期模仿英國的模式,被很多人誤以為的“免費醫療”。
關于英國“免費醫療”的問題,筆者以前的文章其實大致講過。英國現在的醫療體系其實是成型于二戰以后的福利資本主義時期。冷戰時期,為了緩解社會主義陣營良好的人民福利對毗鄰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形成的強大道義壓力,遏制此起彼伏的工人階級抗爭(特別是中國的紅色風暴的感召),西歐資產階級才被迫對民眾作出妥協,實行高福利制度,其中就包括醫療福利。
歐洲的“五月風暴”
所以,福利資本主義從來不是資產階級的“良心發現”,而是國際共運的外在壓力以及西歐各國內部工人斗爭的結果。
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國際共運逐漸陷入低潮;隨著蘇東劇變、全球化下產業外遷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推行,西歐各國的高福利政策大幅縮水,其中,自然也包括醫療福利。借助全民免費醫療,英國女性人均壽命達到82.9歲,男性平均壽命達到79歲,大大高于頭號帝國主義美國。
英國的免費醫療制度外殼雖然得以保存至今,但英國自80年代以來,衛生領域的財政投入裹足不前,有些財年甚至會往下砍,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下,實際上是壓縮了衛生投入。英國每年在衛生醫療領域的開支占GDP的比重是9%-10%,比其它歐洲國家都低,這得感謝新自由主義的兩大頂級推手之一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
有限的醫療投入必然導致沒有充足的資金新建醫院或養活更多的醫生,來滿足民眾的醫療需求。以2015年為準,英國每千人擁有醫生數為2.8人。低于經合組織3.3人的平均值,而其他幾個西歐國家則明顯高于這一數值,奧地利5.1人、挪威4.4人、瑞典4.2人、德國4.1人、西巴亞3.9人、意大利和冰島3.8人;實行社會主義免費醫療的古巴是6.7人,就連經濟困難的朝鮮也有3.7人;而中國為2.59人,醫療開支占GDP最高的美國卻只有2.4人(是不是很諷刺?)。
在公共投入越來越不足的情況下,公立醫院的醫療資源當然越來越緊張,富人可以去私立醫院,窮人則只能去公立醫院排隊。這就是被中國的某些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所攻擊的“英國免費醫療效率低下”,他們還以此來為中國不實行“免費醫療”辯解。
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對福利和民主的進攻,實際上是一個全球的現象,壟斷資本財團在社會公共事務上有了越來越多的發言、實際決策權力。而新自由主義同樣席卷了香港和內地,使得香港在醫療體系上經歷了與英國類似的變遷。
香港公共醫療體系的改善,得益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民眾的反英抗暴斗爭,迫使殖民者和大資本家不得不改善底層的待遇,其中就包括仿造英國建立起免費的全民醫療體系。
上圖:1967年香港國慶節的情景,毛主席像和標語是香港工人自己掛上去的,照片中的港英警察面對旁邊的毛主席巨幅畫像,是無奈還是膽寒呢?
1974年,香港醫療體系的基調形成,《香港醫療衛生服務的進一步發展》白皮書問世,修訂后的醫療政策目標是——保障及促進整體的公眾健康,以及確保向香港市民提供醫療及個人健康設施,特別是那些須依賴資助醫療服務的廣大底層市民。
2000年前后,香港開始對原有的醫療體系進行市場化改革。而今的香港已非政府主導,公共醫療和私人醫療的總開支水平平分秋色。但因為香港同樣存在更加嚴重的貧富分化和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底層市民仍然去公立醫院排隊。2014年12月,香港《自愿醫保咨詢文件》指出,香港約88%的住院服務由公立醫院提供;但截至2012年,香港有48.3%的注冊醫生在私人醫療機構工作(見香港衛生署《衛生醫療服務人力資源統計》),私人醫療機構的診費“主要由有負擔能力的市民自付”(見2010年12月公布的(香港)《基層醫療發展策略文件》)。
大批底層市民因為經濟能力有限被迫擁擠到投入越來越低的公立醫療機構,正是香港公立醫院變得“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如此才造成江迅在病故前遭遇公立醫院的“低效”,“12小時后主診醫生才出現”。
筆者不知道江迅在病危時選擇去公立醫院是因為“心血來潮”,還是因為其經濟能力一樣有限。
江迅在天有靈的話,能反思到香港的“新自由主義”嗎?而江迅生前卻著實充當了新自由主義和西方普世價值的重要鼓吹手角色。
江迅供職的《亞洲周刊》原是英文《亞洲周刊》(Asiaweek)的姊妹刊物,由美國傳媒巨頭時代華納集團創立。1994年1月,香港明報企業集團與時代華納達成收購中文《亞洲周刊》協議,明報企業獲得該刊控制權。
說起《明報》就不能不提到金庸,就不能不提到上世紀60年代參與香港左右論戰的《明報》和《大公報》。筆者從不懷疑金庸先生的愛國立場,但金庸與《明報》的“老右”立場,當然也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由這段歷史公案再來考察、理解《亞洲周刊》和江迅的真實立場也就不難了。
江迅,1947年生于廣東番禺,上海知青,1974年起先后任職于上海第二醫學院、《文匯報》、《文學報》,在上海從事文學和新聞工作20余年。1994年移居香港,任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員,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董事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員。
以上是中國作協下屬的“中國作家網”對江迅的簡介。筆者了解江迅,是從江迅的幾篇重磅報道開始的。
2008年,江迅專訪馬立誠,稱“政改”不能再延誤時機:
2009年,江迅又拋出一篇公開誹謗大陸“毛左”和左翼網站的報道,江迅的老朋友楊錦麟當時還在鳳凰衛視的《有報天天讀》節目中,引述了江迅的這篇報道,更是直呼“毛左網站”之類的詞。:
從大陸移居香港、非常熟悉大陸輿論生態的江迅,不可能不知道大陸“毛左”正是新自由主義的激烈反對者,也不可能不知道這樣的“誹謗”意味著什么——按照這篇文章標題所言,甚至直接可以關閉這家“毛左”網站了,這恐怕正是江迅所期望的。
2010-2012年期間,江迅還有幾篇有關上層的文章,鑒于內容敏感就不列出了,感興趣的自己去搜索。通過這些出自江迅手筆的報道,人們不難看出江迅愛什么、恨什么,江迅的“老右派”立場也就很清晰了。
2010年,江迅還曾牽涉到一場輿論官司:
對于江迅事后的表態言論,在大陸生活的人其實是難以理解的,江迅竟會“以此為恥”?
其實這毫不奇怪,無奈這個“老右派”在香港工作生活,你把國內的“炎黃系”、“南方系”的那幫“老右”放到香港或者海外去,他們的言論恐怕跟江迅比,只會一個比一個出格。
觀察者網2015年曾經給江迅開過一個專欄,里面只收錄了一篇文章:
單從這篇文章看,你能看出江迅賣國嗎?相反,人家是很“愛國”的。
2020年底,江迅在香港商務印書館推出了新書《在黑夜點燈——香港這一年不能忘卻的他和她》,是對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光頭警長”劉澤基、“十四億人茶餐廳”老板娘李凱瑚等六人的訪談錄,嚴厲抨擊了那些禍港、亂港的青年。
江迅與內地的很多名人都交好,例如莫言就曾盛贊“江迅兄寧愿荒廢一枝筆也要做朋友們的后勤司令”;今年4月2日,江迅還在《亞洲周刊》推出文章《方方捐出武漢日記九成稿酬》,為方方洗白造勢。
北大的張頤武教授在文章《香港<亞洲周刊>為方方捐款造勢的真正動機》中指出:
這種荒唐的洗白當然是最下作的編造,她和她背后的勢力就是要在世衛組織報告的公布前后的這個關鍵時間透露五個月前的捐款消息,由此洗白自己,用偽證攻擊報告。他們精心謀劃了這個傳播行動。現在用《亞洲周刊》報道正是這個行動的關鍵一步。
他們確實做絕了,確實是內外結合,精心策劃,巧妙執行。一定要在世衛組織報告出臺前后掀起大風浪。
盡管方方的“日記”客觀上起了給帝國主義遞刀子的作用,但很難說她有這個主觀動機,只是階級立場催生了她的寫作角度和對事物評述的立場。江迅、方方、莫言之流,人家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更“愛國”。
只是老右派們秉持的普世價值和“世界主義”立場謀求向西方資本主義接軌,在帝國主義橫行的當下,很容易表現為“賣國主義”。但很多精英仍然對“世界主義”仍然是深信不疑,時刻還盼望著與美帝國主義“修復關系”,“回到正常軌道”,如此,方方、江迅之流自然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橋梁。
本文標題稱呼江迅為“愛國者”,當然是沒有任何錯的。而這樣的“愛國者”江迅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問題的樣本:
十年前江迅把他筆觸的矛頭對準大陸“毛左”,間接為新自由主義站臺的時候,絲毫沒有回身看看資本寡頭“李家城”對香港市民的荼毒,這終于間接地讓江迅在今日嘗到了入公立醫院被延誤治療的惡果;而這樣的江迅對于香港底層的青年其實是沒有太大說服力的,這樣的“愛國者”也不足為訓。
看不起工農群眾,不肯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固守“一己之私”的知識分子們注定是“狹隘”的,缺乏真正的反思能力的。江迅在天有靈的話,恐怕仍然會固守著自私的立場;只是作為讀過莫言、方方、江迅文字的青年們,大多將來還是要在工農階層打拼,是真正需要“反思能力”的。而反思就請先擺脫江迅之流的反毛文字誤導,從重新認識毛主席開始。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