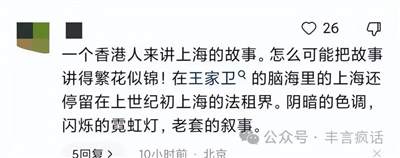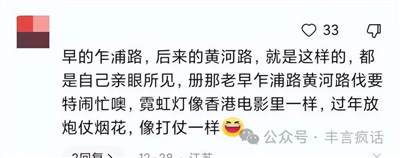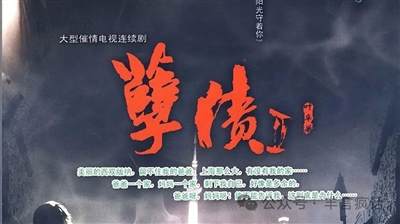網(wǎng)上對(duì)《繁花》的爭論,陷入了一個(gè)誤區(qū),那就是反復(fù)去質(zhì)疑,這到底是不是90年代的上海。
諸如此類的,還有這是香港人眼中的上海,小布爾喬亞眼中的上海。
如果按照這個(gè)思路走下去,那就必然形成“外地人有沒有資格批評(píng)上海”以及“上海人如何捍衛(wèi)歷史傳統(tǒng)”兩大陣營。
比如,欣賞王家衛(wèi)是有門檻的啦,你們不懂海派文化啦,聽不懂上海話就別張口啦。
之所以說這個(gè)問題沒有必要,是因?yàn)椤斗被ā凡⒉皇且徊繗v史正劇,它不需要完整反映歷史事實(shí),只要滿足觀眾的胃口和好奇心就夠了,當(dāng)成現(xiàn)代版的《瑯琊榜》爽一爽,也無可厚非。
而且,我們能看出王家衛(wèi)已經(jīng)能努力地去講一個(gè)故事了,什么裝逼腔調(diào)、光影美學(xué)、小資做派,這些只是香精和佐料,屬于他的個(gè)人風(fēng)格,多一點(diǎn)和少一點(diǎn),都無傷大雅。
但是,《繁花》依然是值得批判的,并不是因?yàn)樗鼱€,而是它留下了一個(gè)巨大的遺憾。
尤其是宣傳上,把《繁花》當(dāng)成了時(shí)代精神和上海群像的代表時(shí),確確實(shí)實(shí)鬧出了烏龍,把玩笑開大了。
《繁花》的問題,是不是上海風(fēng)格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丟掉了上海文藝的金字招牌,那就現(xiàn)實(shí)主義傳統(tǒng)。
大家好,我是豐兄,這期給大家聊聊上海影視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以及《繁花》的問題。
中國的影視有兩座高峰,一座是國家力量主導(dǎo)下的大制作,比如經(jīng)典的四大著名系列,大決戰(zhàn)系列,每一部都是大手筆,完全不計(jì)成本,硬是在落后的時(shí)代,徒手搓出來的佳篇巨著。
另一座高峰則來自于上海,上海的影視不喜歡架空,不喜歡講歷史,更不喜歡討論意識(shí)形態(tài),它關(guān)注的只有一點(diǎn),那就是生存問題,是一日三餐,冷暖溫飽,賺錢多少。
它喜歡以小見大,通過兩性、小三、房價(jià)、物價(jià)、貪官、交易、商戰(zhàn)這些具體的元素,去批判現(xiàn)實(shí)。
為什么上海會(huì)成為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文藝的誕生地呢?《上海的狐步舞》里,這樣評(píng)價(jià)上海,“上海,造在地獄上面的天堂!”
從一百年開始,這里就有燈紅酒綠和天堂地獄。資本家、姨太太、少爺、舞女、工人、水手、強(qiáng)盜、綁匪、電影明星、娼妓掮客、印度巡捕,你幾乎可以找到一個(gè)社會(huì)所有的身份。
一面是有產(chǎn)階級(jí)的荒淫無度,腐敗墮落;一面是無產(chǎn)者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一面是有產(chǎn)者在華東飯店摸牌賭博、花天酒地;一面是無產(chǎn)者慘死在大柱下無聲無息。
人們?cè)谄扑楹统翜S中掙扎,一不小心就不會(huì)被拉下地獄。所以不管是封建官僚來,還是帝國主義來,還是殖民者來,這里的人最關(guān)心的,就是如何生存下去。
中國最好的無聲電影,是三十年代上海拍攝的《神女》,它講一個(gè)女人的故事,而且是所謂比較下賤的職業(yè),妓女。
作為社會(huì)底層的暗娼,為了帶自己的兒子活下去,躲避警察的追捕,又不幸落入了流氓的手中,所有鄰居都排斥她,認(rèn)為她骯臟不堪,兒子也被同齡人排擠和嘲笑。最終她被逼無奈,下決心逃離這個(gè)泥潭,失手殺死了掌控她的男人。
兩年之后的《新舊上海》,更是精彩,一幢破舊的公寓樓里,住著六戶人家,有在歌廳上班入不敷出的舞女,有被拖欠工資的小學(xué)教員,有每天用體力勞作的黃包車夫,也有沒事就閑著嗑瓜子的包租婆。
就在這么一棟小小的樓里,卻有著各類社會(huì)問題橫截面,炒股失敗的,投資被騙的,情場失意的,用移鏡及貓眼、嬰啼等巧妙轉(zhuǎn)場,經(jīng)濟(jì)蕭條下,底層人真是朝不保夕。
所以,對(duì)他們來講,生存最重要,不論外面的世界怎么變,小家庭里每月一塊錢的豆腐漿一定要喝,紅燒蹄髈要爭取吃上。
你看,過去的舊上海,今天的新上海,大家關(guān)心的都是這個(gè)問題。
建國后,上海電影與延安電影分庭抗禮,繼續(xù)現(xiàn)實(shí)主義批判,兩邊互相打擂臺(tái),北方拍出《永不消逝的電波》《林家鋪?zhàn)印罚戏骄蛣?chuàng)作《花好月圓》《球場風(fēng)波》《女籃5號(hào)》。
兩邊其實(shí)都是左翼傳統(tǒng),只不過一個(gè)是延安革命主義,一個(gè)是上海左翼文化,立場都站在人民這邊。
但是,延安傳統(tǒng)勢頭過猛,上海這邊后來拍的《舞臺(tái)姐妹》《不夜城》《北國江南》,都被批判。上海派導(dǎo)演沉寂了一段時(shí)間。
直到90年代,上海影視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傳統(tǒng)重新回歸。
東方風(fēng)來滿眼春,南巡講話定了調(diào)子,浦東要變成上海,甚至超越上海。
陸家嘴高樓林立,東方明珠拔地而起,南浦大橋飛架黃浦江。十年間,上海動(dòng)遷,大批本地人從市中心向郊區(qū)遷移,遷了300多萬人。而更多的精英人士和打工仔,則從外地進(jìn)來。
那時(shí)候是怎么說的,“未來的上海,內(nèi)環(huán)講英語,中環(huán)講普通話,外環(huán)才講上海話”。這也就是《繁花》的時(shí)代背景,但《繁花》沒提到的是,彼時(shí)的上海,既狂歡,也壓抑。
從鄉(xiāng)里到城里,中國要走向都市化,那么,上海無疑就是最好的舞臺(tái),都市影視劇,成了一朵最耀眼的花。
上海的電視劇,決定繼續(xù)寫時(shí)代。《孽債》里,十年一夢,返城洶涌,改革開放,恢復(fù)高考,但城市戶口注定有限,曾經(jīng)的知青,面臨人生的兩個(gè)重大選擇。
第一種,忘掉當(dāng)初是從城里來的,忘掉自己讀書人的身份,以后就待在農(nóng)村和土地過一輩子。
第二種,舍親棄愛,悄悄返城落戶,運(yùn)氣好還可以分配工作,可以再參加高考,一旦上了大學(xué),響應(yīng)政策去經(jīng)商下海,說不定就成為《繁花》的寶總了。
1995年,《孽債》一播出,就創(chuàng)下收視率新高,當(dāng)時(shí)的人看得入迷, 上海電視臺(tái)曾因播出“群星愛心演唱會(huì)”節(jié)目,把《孽債》停播一天,雖然事先電視臺(tái)多次打出字幕向觀眾說明,上海觀眾還是急壞了,瘋狂打電話給電視臺(tái),說只要當(dāng)晚播,再晚也沒意見。
上海電視臺(tái)損失了整整200萬元的廣告費(fèi),將每晚播一集改成兩集,這才讓觀眾解饞。
1991年的《上海一家人》,把故事背景放在了解放前,貧苦農(nóng)民沈川兒帶著女兒若男闖蕩上海灘,同樣都是混跡這座“冒險(xiǎn)家樂園”,《繁花》里只有流于表面的珠光寶氣,《上海一家人》卻在真正描寫時(shí)代。
若男住在閘北漏風(fēng)的房子,棚戶區(qū)集體排隊(duì)倒馬桶,上海女裁縫的事業(yè)就從這里開始,你可以看成一部舊社會(huì)的“杜拉拉升職記”,但卻沒有神仙戀愛,妖怪打架,爽劇其實(shí)也可以有另一種拍法。
1990年播出的《十六歲的花季》,雖然是講青春和愛情,但觸及到了出國熱、婚外情、教育改革、知青子女回滬、教師下海經(jīng)商、學(xué)校破墻開店搞創(chuàng)收、贊助生等等的時(shí)代風(fēng)貌。
上海都市現(xiàn)實(shí)主義題材,是中國影視開出最別致的一朵花。西北的《關(guān)中匪事》《高興》這樣的電視劇,偏向土地和歷史;而像《奮斗》《正陽門下》這樣理想化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劇目,似乎又了一絲殘酷。
都市進(jìn)行時(shí)的上海影視,完美擊中了正在轉(zhuǎn)型期的中國人的復(fù)雜心理。
到了新世紀(jì),上海影視繼續(xù)在現(xiàn)實(shí)主義這條路上狂飆,最終誕生了一部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代表作《蝸居》。
海藻那句“人情債,我肉償啦!從現(xiàn)在開始我就步入職業(yè)二奶的道路了!”,過于震撼,而且這樣驚悚的臺(tái)詞,還有很多,隨便一個(gè)元素拎出來都堪稱大膽。這部劇在尺度上挑戰(zhàn)了道德和更深處領(lǐng)域的中國社會(huì)。
可惜的是,《蝸居》引發(fā)的一場社會(huì)海嘯,竟然是上海影視乃至中國現(xiàn)實(shí)主義影視的最后高潮。
當(dāng)時(shí)很多上海觀眾,對(duì)電視劇提出質(zhì)疑,說這根本不像上海,事實(shí)上,編劇六六也承認(rèn),自己只在上海待了六個(gè)月,對(duì)上海并不了解。但是,外地的觀眾幾乎集體性認(rèn)為,江州就是上海。
這跟《繁花》恰恰相反,上海人說,沒有人比我更懂上海,外地觀眾則不滿,表示你這明明就是民國。
事實(shí)上,他們都沒錯(cuò),上海人看到的是童年濾鏡,外地人覺得劇情太抽離。這并不是看滬語版就能解決的,根本還在于《繁花》缺少了一層現(xiàn)實(shí)主義。
需要說明的是,現(xiàn)實(shí)主義并不是現(xiàn)實(shí)本身,現(xiàn)實(shí)主義影視并不是現(xiàn)實(shí)的直接復(fù)制,不然就成了記錄片。現(xiàn)實(shí)主義需要直擊時(shí)代內(nèi)核,以及生存問題。
新世紀(jì)以來,上海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影視走向衰敗,如果說《蝸居》算是一次回光返照,那么,此后現(xiàn)實(shí)主義徹底走向了半衰期。
比如《我的前半生》《歡樂頌》《三十而已》,盡管它們披著現(xiàn)實(shí)主義外衣,但扒開這些裝點(diǎn)和門面,里面全是一個(gè)個(gè)瑪麗蘇。
小說《繁花》作者金宇澄,在東北下鄉(xiāng)八年,跟勞改犯們一起生活,落到底層,再返回上海的工人新村,南來北往,一把年紀(jì), 就像巴爾扎克小說里一個(gè)海員回來,巴黎貴婦人要他講故事。
金宇澄會(huì)講些什么呢?那指定不可能是熱血沸騰的創(chuàng)業(yè),他要書寫的上海“城市曖昧層面”的灰色地帶,小說一開頭,“獨(dú)上閣樓,最好是夜里”,半生浮沉,娓娓道來。
現(xiàn)實(shí)主義不是說一定要寫窮人,也不是不能雕梁畫棟,關(guān)鍵要突出“難”,而不是“爽”。
《大明王朝1566》講的是朝堂,但算的是經(jīng)濟(jì),國庫虧空,巨大的窟窿要補(bǔ)上,從皇帝到臣民都很著急,所以嘉靖說,朕知道你們難,朕也難,我們都勉為其難吧。接下來才有通敵倭寇,改稻為桑,嚴(yán)黨和清流大戰(zhàn),我們看到大明朝已經(jīng)爛了。
90年代的上海也很難,光是職工就有一百萬人下崗,當(dāng)時(shí)市長的原話是,“我現(xiàn)在是一天一天感到捉襟見肘啊!這兩年,政府的虧損補(bǔ)貼直線上升,去年增加9億多元,今年增加13.7億元,搞不下去了。”
因?yàn)殡y,所以要改革,改革該“放”還是該“收”,產(chǎn)業(yè)如何轉(zhuǎn)型,要不要大力發(fā)展第三產(chǎn)業(yè),金融改革要不要邁大步?這些是當(dāng)時(shí)上海社會(huì)的大討論。
《繁花》是都市劇,當(dāng)然不需要直接描述這種歷史背景,但是你宣傳口徑上是“現(xiàn)實(shí)主義”,那就應(yīng)該有很多側(cè)寫。
《十六歲的花季》為什么比《流星花園》強(qiáng)一萬倍,那是因?yàn)楝F(xiàn)實(shí)劇的生態(tài)位,就是會(huì)碾壓偶像劇。
《十六歲的花季》劇情很放得開,這些來自于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
導(dǎo)演張弘寫劇本的時(shí)候,進(jìn)行了采樣調(diào)研,他在一所師范學(xué)校的“新疆班”,看到了這樣的場景:周末放學(xué)后,學(xué)校門口停了一排摩托車。一些個(gè)體戶把班上的女孩子接走了。
因?yàn)檫@些知青子女回到上海后,在落戶問題上遇到了困難。她們大多寄住在親戚家,小小年紀(jì)就飽嘗了寄人籬下的滋味。
有人問導(dǎo)演為什么要拍這些,張弘回答,“因?yàn)橹袑W(xué)生已經(jīng)和社會(huì)有聯(lián)系了。他們對(duì)社會(huì)對(duì)家庭對(duì)教育等等問題都有自己的看法了。”
《繁花》我們能看到“社會(huì)”嗎?看不到,它是青春劇,偶像劇,瑪麗蘇劇,商戰(zhàn)爽劇,唯獨(dú)不是現(xiàn)實(shí)主義劇。
寶總做外貿(mào)就是為了汪小姐那一出戲,確實(shí)很讓人出戲,這個(gè)套路已經(jīng)爛俗到了十幾年前青春疼痛文學(xué)的地步了。
“你說應(yīng)愁高處不勝寒,我便拱手河山討你歡”。郭敬明狂喜,王家衛(wèi)降格到了和自己同一水平。
雖然不至于要像小說中主配角人均兩三個(gè)性伴侶,但也不用拍成小學(xué)生般的天真。
《繁花》的小說能拿到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僅僅是因?yàn)槊鑼懥艘环N地方生活嗎?又或者是舊瓶裝新酒懷舊嗎?當(dāng)然不是,是因?yàn)樗泻軓?qiáng)的時(shí)代感。
從公私合營到六十年代中期,上海的民族資本家是一直可以領(lǐng)股息的,阿寶的爺爺和父親,都能享受到相當(dāng)富足的生活。從富家子弟到落魄少年,從市中心體面的大房子,搬到了曹楊工人新村,這是阿寶成長的歷史背景。
當(dāng)電視劇把歷史背景拋掉后,不管是在“至真園”里的酒席上,或者是“夜東京”的飯桌上,這些人來來往往,顯示著流水席的繁華,整個(gè)生活卻并沒有著落。
90年代消費(fèi)主義的上海,浮華煙云,落花流水,這些生活、這些故事都十分傳奇?zhèn)魃瘢⒉恢赶驓v史,因?yàn)闅v史已然虛空消散了。
上海一直有兩種歷史傳統(tǒng),一種是從上海開埠開始,到上世紀(jì)二三十年代形成的海派文化。另一種是1949年到1990年代初形成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傳統(tǒng)。
這兩個(gè)傳統(tǒng)區(qū)別很大,今天人們懷舊,當(dāng)然不希望是后面一種,更喜歡前面那種,宏大敘事解體后,我們只能去懷念曾經(jīng)的上海舊夢。
畢竟我們可能已經(jīng)不習(xí)慣再看到棚戶區(qū)的上海人倒馬桶,黃河路上的五光十色,才是消費(fèi)時(shí)代人們最喜歡的景色。
除此之外,《繁花》能引起這么大討論,還在于一種矛盾,上海的學(xué)者許紀(jì)霖說過,“上海人”和“中國人”,有時(shí)候是一對(duì)沖突概念。
清末的時(shí)候,上海有個(gè)地方賢達(dá)李平書,去拜見李鴻章,李鴻章很欣賞他,臨走前拍拍他的肩膀,對(duì)他說:“你不像一個(gè)上海人。”這是李鴻章對(duì)李平書最高的評(píng)價(jià)。
這個(gè)評(píng)價(jià)在今天依然如此,上海身份對(duì)中國人來說很特別。
1949年之前,當(dāng)整個(gè)中國還處于農(nóng)業(yè)社會(huì)時(shí),上海已經(jīng)是資本主義下的十里洋場了,別的地方是從封建社會(huì)直接到社會(huì)主義,上海則是從資本主義進(jìn)入到社會(huì)主義。
到今天,上海的氣候是不是還跟別處不一樣,這就是引起人們爭論的地方了。
但是,《繁花》是不是上海,真的不重要,抽離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繁花》,好看是好看的,但那是大量香精和佐料堆出來的,就像端上來一道辣子雞,滿盤都是花椒和辣椒,你要是想吃雞塊,就特別費(fèi)勁。
當(dāng)人們繼續(xù)懷念上海舊夢的時(shí)候,我想到的是上海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想到曾經(jīng)的鞭辟入里,辛辣淋漓,這種力度可能再也回不來了。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yùn)行與維護(hù)。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