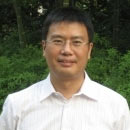阿凡達迷們沒看懂《阿凡達》
中國人是地球上的"阿凡達"嗎?
在《阿凡達》中,卡梅隆導演藝術(shù)地表達了對西方文化與東方文明融合的期盼。但問題是,中國人還能找回自己的精神圣樹嗎?這是卡梅隆留給西方人和東方人的共同課題,歷史等待我們?nèi)ソ獯穑绻覀兓卮鸩涣耍覀兒芸赡芫筒辉贂袣v史。
張庭賓
中國人,是地球上劫后余生的納威人嗎?
在醞釀“庭賓透世”時,從沒有想過會寫一部電影。然而,看了孟隋先生寫的《“阿凡達是好萊塢主義的殖民寓言》(以下簡稱《殖民寓言》)之后,卻受啟發(fā)——發(fā)現(xiàn)它是一個絕佳的透世表達窗口。不怕說句會得罪阿凡達迷們的話,真正看懂了《阿凡達》的人,是孟隋先生。
《殖民寓言》深刻到深邃地指出:“美國人很容易看出,《阿凡達》的故事與美洲殖民者屠殺、驅(qū)逐印第安人的歷史很相似。更廣義地看,《阿凡達》可以看作一個關(guān)于西方文明的殖民寓言。納威人的形象代表了西方人對所謂的野蠻民族的想象;納威人的神靈信仰和巫術(shù)也是“東方式”的,類似于禪宗的直覺和頓悟;納威人崇拜的母親樹有點像印度的菩提樹(智慧樹),他們飛行乘用的怪獸類似西方人想象的中國‘龍’……”
卡梅隆導演留下余味的一層窗戶紙被孟先生輕易地捅破了,納威人不在虛無縹緲的潘多拉星球上,就在地球上,它可以是印第安人,可以是中國人,可以是印度人,只要他們的“圣樹”下有地球主宰者需要的財富和資源,它們就可以被 “納威人”,這個老套路的殖民故事直到今天仍在上演,只不過殖民的工具升級了而已。
地球上被幾乎消滅的納威人
納威人何嘗不是印第安人呢?
經(jīng)典的故事要從北美感恩節(jié)說起。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號船滿載清教徒102人到達美洲。1620年和1621年之交的冬天,他們處在殘酷的饑寒交迫之中,活下來的移民只有50來人。這時,心地善良的印第安人給移民送來了生活必需品,還特地派人教他們怎樣狩獵、捕魚和種植玉米、南瓜。在收獲季節(jié),白人舉辦了對印第安人的“感恩節(jié)”。
可是,當白人在北美站穩(wěn)了腳跟,他們是怎么“感恩”的呢——消滅這些印第安人!在其后的一個多世紀中,2000多萬印第安人在被屠殺和驅(qū)逐中消亡。1779年,喬治·華盛頓指示John Sullivan少將攻打Iroquois印第安人時說:(假如)將廢物(指印第安人)放到所有定居點附近,…那么整個國家將不僅僅是泛濫成災,而是被摧毀了。…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毀前不要聽取任何和平的建議。
美國的獨立宣言中鐫刻著如此偉大的語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nèi)舾刹豢勺屌c的權(quán)利,其中包括生存權(quán)、自由權(quán)和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但在同一篇獨立宣言中也寫下了非常殘忍之言:“他(英國統(tǒng)治者)在我們中間煽動內(nèi)亂,并竭力挑唆殘酷無情的印第安蠻子來對付我們邊疆的居民,而眾所周知,印第安人作戰(zhàn)的準則是不分男女老幼、是非曲直,格殺勿論”。
這一段宣言,為北美白人對印第安人的種族屠殺確定了法理基礎。然而,他們過于大意的是,他們忘記了同時取消“感恩節(jié)”——現(xiàn)在他們無法自辯為何要對印第安人感恩。
就像《阿凡達》中的地球人一樣,上校和他的軍隊憑借著先進的武器,將原來北美大陸上的主人——印第安人屠殺的幾乎殆盡。兩者間共同的真邏輯只有一個——你們(納威人或印第安人)擁有著我們需要的土地、礦產(chǎn)和財富。殖民主義的真相就是這么赤裸裸。
這就是美國立國時的“人人平等”——印第安人不被當成人,是一群像納威人那樣長著長尾巴的猴子;而黑人則是奴隸,他們的功用就是為白人永無休止地勞作。
中國人——絕處求生的地球納威人
地球人那些幾近被滅種的納威人,不僅僅有美洲的印第安人,還有澳大利亞的土著人,來自歐洲的占領(lǐng)者一度將他們從75萬人消滅到7萬人。
與《阿凡達》中相似的是,地球上也有在最后關(guān)頭絕處求生的納威人,他們就是中國人和印度人。作為人類綿延時間最長的文明,中國、印度人與自然和外部世界和諧共處,沒有殖民擴張的興趣,按照自己的文明方式生存。
在這種文明中,激烈的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是不被鼓勵的(或者被局限在少數(shù)官僚內(nèi)斗中),人與自然之間是和諧相處的;技術(shù)的進步是不被歡迎的——火藥是中國人最先發(fā)明的,但在“兵者不祥之器”的理念指導下,中國人把它的花樣技巧都用在歡慶節(jié)日的煙花上。
在古代東方文明中,最高智商的人追求的是羽化成仙,修道證佛,即超越物質(zhì)羈絆與肉體枷鎖,實現(xiàn)人的精神小宇宙與大宇宙精神的融合。這種對于精神幸福的追求吸引了從釋迦摩尼王子到清朝順治皇帝拋棄王位去追求;第二等智商的人才追求王侯將相、功名利祿;第三等智商的人對社會大眾則采取了“民使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家方略,你可以說它是愚民政策,其實是貫徹老子的“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智,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的思想。這是中華文明5000年依然可以自給自足、綿延不斷的核心秘密。
然而,這種東方內(nèi)斂自足文明在近現(xiàn)代遭遇了西方文明后,便一路潰敗。原因也不復雜,西方文明是外向征服性文明,從柏拉圖的《理想國》開始,西方就確立了他們的正義觀——城邦的正義合法性在于,它內(nèi)部可以民主制衡,團結(jié)本城邦人民,實現(xiàn)向外的征服和財富占有,并向內(nèi)分配戰(zhàn)利品,每個人都可以有新增的物質(zhì)福利。再加上日后基督教“一神論”的排他性,它必然鼓勵向外的殖民和掠奪,進而推動在物質(zhì)武器上的不斷進步。
由于在內(nèi)部凝聚力和外部競爭力上遙遙領(lǐng)先,西方文明一度形成了對其它文明絕對的競爭優(yōu)勢。從1840年以后發(fā)動了對華的一系列的戰(zhàn)爭,并將中國人在20世紀初逼迫到亡國滅種的邊緣。
與納威人不同,中國人的絕地求生沒有地球人派出的“阿凡達”來領(lǐng)袖。而是在殘酷的現(xiàn)實面前,那些曾經(jīng)沉迷于求仙問道的最高智商的國人,當他們意識到偌大的中華天下已經(jīng)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時,他們不得不領(lǐng)導中國人奮起反抗。
由于中國太大,人口太多,“地球人”需要借“阿凡達”來統(tǒng)治,這反過來也給了努力救亡圖存的中華精英學習西方現(xiàn)代競爭體制和技術(shù)的機會——從西方資本主義激發(fā)人的惡性競爭的市場經(jīng)濟;到推崇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的現(xiàn)代化思維;到以捍衛(wèi)勞動和弱勢者利益的烏托邦理想。
然而,由于西方文明在其核心是靈魂孤獨的,它無法實現(xiàn)個人的精神小宇宙與大宇宙精神的融合,這也讓西方頂尖的哲學精英,《西方的沒落》作者斯賓格勒無比的悲哀——它可以征服整個世界卻恰恰唯一征服不了自己的靈魂。這使得中華精英一旦看透了西方文明,他就不可能成為西方虔誠的頂禮膜拜者。就像一位大學生不會甘心去膜拜一位小學生一樣。
中華精英在一切可能的領(lǐng)域?qū)W習西方的競爭文明方式。并通過對外對內(nèi)激烈的競爭和戰(zhàn)爭,重樹了一代西方式生存的中華強人,并在這些強人的領(lǐng)導下使民族重獲自由和解放。
但在地球上的納威人與殖民者的較量并沒有結(jié)束。
中國人還能找回自己的精神圣樹嗎?
在電影中,納威人將貪婪而自私的殖民者趕回了即將毀滅的地球,可是,納威人真的勝利了嗎?
孟隋先生的《殖民寓言》中最觸動我的一段話是這樣的——“殖民的文化后果就是世界的同一化,當敬畏生命、崇尚自然的納威人也開始使用機槍和對講機的時候,已經(jīng)意味著西方文明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當入侵者被趕出了潘多拉星球。但導演還是意味深長地讓納威人永遠失掉了他們的“母親樹”。”
同樣的道理,在中國人以西方的武器反對殖民者,當中國人以西方的方式開汽車和喝可樂,當中國人以西方的方式制造三聚氰胺,當中國人以西方的方式與西方爭奪資源時,中華文明是勝利了還是失敗了呢?
這已經(jīng)是東方內(nèi)斂和諧文明的失敗。就像《阿凡達》中,我們雖然以慘烈競爭的方式獲得了某種勝利,但是,在戰(zhàn)爭中,他們和我們共同摧毀了我們的“母親樹”,我們還能重建我們的母親樹嗎?
更何況,現(xiàn)實中的東方人根本沒有任何資格自認為勝利者。在這個人類唯一的家園——地球上,如果任由西方式征服和競爭文明膨脹,如果任由中國人、印度人或者黃種人、黑種人、紅色人都變成西方人,都要靠競爭和掠奪生存的話,那么,在外太空根本不存在潘多拉星球的情況下,人類的出路幾乎只剩下西方化的地球人自相殘殺。
《阿凡達》這部影片的真正意義正在于此。如今,西方精英忽然發(fā)現(xiàn),當西方文明在地球上獲得了空前成功后,人類正在快速消滅自己生存的最后空間。
這使他們產(chǎn)生前所未有的危機感,這種恐懼催生了號稱“人類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機會”的哥本哈根會議,也催生了西方主流文化對殖民主義的空前反思——這就是電影《阿凡達》,卡梅隆導演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只用了160分鐘上了一堂無比精彩的課,讓地球上的億萬觀眾參與進來反思。
在《阿凡達》中,卡梅隆導演藝術(shù)地表達了對西方文化與東方文明融合的期盼——正如地球人在電影中兩次與納威人的結(jié)合,第一次是物質(zhì)基因的肉體結(jié)合;第二次是通過幸存的圣樹,實現(xiàn)了靈魂的結(jié)合。這會給現(xiàn)實以啟示,但是,中國人已經(jīng)不可能回到古代,我們還能找回自己的精神圣樹嗎?
這是卡梅隆留給西方人和東方人的共同課題,歷史等待我們?nèi)ソ獯穑绻覀兓卮鸩涣耍覀兒芸赡懿粫儆袣v史。(聯(lián)系郵箱[email protected])
孟隋:《阿凡達》 好萊塢主義與殖民寓言
東方早報
好萊塢商業(yè)電影從來都是有一套的,什么樣的起承轉(zhuǎn)合,什么樣的煽情、烘托,什么樣的視覺追求——雖然在不同的電影中有著不同比例的配置,但好萊塢的商業(yè)電影絕大多數(shù)都走不出這個或許可以稱之為“好萊塢主義”的套路。
最近“好萊塢主義”的家族中又多了一個“史上最昂貴”的成員——《阿凡達》。它的劇情是如此好萊塢,以致讓人觀賞時常常猜到后來的故事情節(jié)。《阿凡達》的整個故事情節(jié)沒有一處不充斥“好萊塢主義”的味道——“愛情拯救英雄,英雄拯救一切”的故事核心仿佛永遠都是好萊塢的真理。《阿凡達》如果不是發(fā)生在潘多拉星球上,而是發(fā)生在地球上,那么它可能就是另一部《勇敢的心》。
爛俗是指好萊塢主義的商業(yè)屬性,但好萊塢之所以是最成功的電影商業(yè)模式,自然也有其過人之處——除了在固定套路和最大的技術(shù)條件許可下的求新求異,好萊塢還喜歡搞一些深刻的東西,來裝飾自己作為商業(yè)片的“深刻性”。求新求異是其賣點(如革命性的3D視覺技術(shù)就是《阿凡達》的一個賣點),而淺顯的“深刻性”是其品質(zhì)保證(我們的國產(chǎn)大片缺的就是這點)。因此,借我們一雙哲學的慧眼,總是能在好萊塢商業(yè)片中收獲淺薄而形象化的“思想”。
美國人很容易看出,《阿凡達》的故事與美洲殖民者屠殺、驅(qū)逐印第安人的歷史很相似。更廣義地看,《阿凡達》可以看作一個關(guān)于西方文明的殖民寓言。納威人的形象代表了西方人對所謂的野蠻民族的想象——納威人拖著一根長長的尾巴,是他們在種族進化中落后的表現(xiàn),電影中也稱其為一群藍色的猴子(blue monkeys);他們的男性拖著一根大辮子,容易讓人想到其原型來自東亞的一些游牧民族,甚至我國的清朝;納威人的神靈信仰和巫術(shù)也是“東方式”的,既類似于東亞游牧民族的薩滿信仰,也類似于禪宗的直覺和頓悟;納威人崇拜的母親樹有點像印度的菩提樹(智慧樹),他們飛行乘用的怪獸類似西方人想象的中國“dragon(龍)”;納威人的外表似乎還綜合了非洲黑人體征和美洲印第安人的飾物習俗。因此,納威人可以算是對西方人想象外域“野蠻民族”的一種綜合。在西方文明中,這種“想象方式”是一個傳統(tǒng),東方總是以野蠻和殘暴的形象出現(xiàn)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在好萊塢有關(guān)東方的電影中,如《奪寶奇兵》、《木乃伊》系列,東方人不是生活在君主專制和貧窮愚昧中,就是總以冷酷、奸詐、惡毒的壞人面孔出現(xiàn)。
恰恰是這種想象,為西方文明的自以為是和殖民擴張奠定了心理和文化上的基礎。《阿凡達》“深刻”反思的就是這點——自以為是的西方人野蠻地打破了納威人的原始生活,納威人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環(huán)境,必須對抗西方人。然而,假如他們要對抗西方人,那么他們就要學會使用西方的機槍、飛機,如果他們不想落后挨打,就注定要被西方文明同化。《阿凡達》似乎道出了,現(xiàn)代西方文明的動力是不斷的生產(chǎn)—消費—擴張,并通過這個鏈條的循環(huán),盡可能地攫取利潤。他們看待野蠻人的傲慢方式,只是對他們這種經(jīng)濟活動作出的文化辯護而已,西方文明試圖把一切東西都卷入這個體系,恰似一種不斷自我繁殖、擴張的,能吞噬一切的致命病毒——在電影中,這種生產(chǎn)—擴張型的文明已經(jīng)把地球給毀掉了,它還要繼續(xù)毀掉潘多拉星球的文明,為了獲得利潤,它在那個星球進行“野蠻拆遷”和肆意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現(xiàn)代西方文明的生存邏輯就是,不斷地再生產(chǎn)、不斷地再擴張,這必然產(chǎn)生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從而在無限的擴張中,加速人類的毀滅——這是生態(tài)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西方文明(或“資本主義文明”)的反思,想不到它竟然也被運用到了電影中,不能不佩服好萊塢編劇們的強大。
《阿凡達》對殖民寓言的重述,對于每一個熟悉世界近代史的人是如此之眼熟,它正是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歷史的寓言表述。殖民的文化后果就是世界的同一化,當敬畏生命、崇尚自然的納威人也開始使用機槍和對講機的時候,已經(jīng)意味著西方文明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是電影總歸要恪守好萊塢主義的準則,給大家留下一個光明的尾巴——西方入侵者被趕出了潘多拉星球。但導演還是意味深長地讓納威人永遠失掉了他們的“母親樹”(mother tree)。
電影歌頌了異族之間的愛情,英雄的意識(靈魂)通過DNA技術(shù)“潛伏”進了納威人的部落,但當他學會納威人的一切后,他愛上了那種文明,最后他竟然成為了反西方的英雄。看來,盡管西方文明有著不光彩的殖民性格,有著濃厚的擴張本性,有著對“野蠻民族”的天生傲慢,但它仍舊可以不斷反思自身,這樣,希望總是有的。《阿凡達》對西方人想象“野蠻民族”的方式進行了一個鏡像反轉(zhuǎn),電影中展示了西方文明的種種丑惡,贊揚了野蠻民族“野蠻中的美好”,但是,也許可以看作根深蒂固的是——救苦救難的英雄仍舊是西方人,仍舊是擁有反省能力的西方文明的另一面。
跳出電影回到現(xiàn)實,我們發(fā)現(xiàn)強勢者不僅比你更懂得怎樣去“血淚控訴”,他們還能重建你對他們的深切認同。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