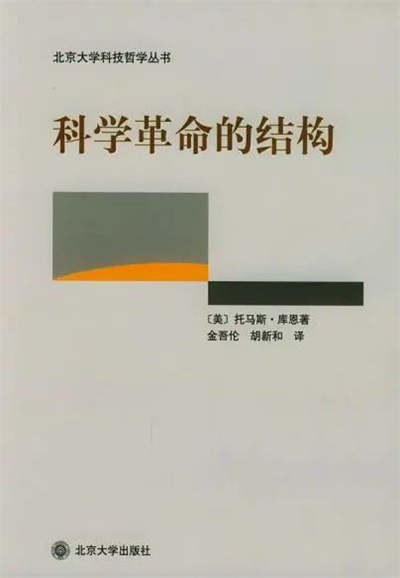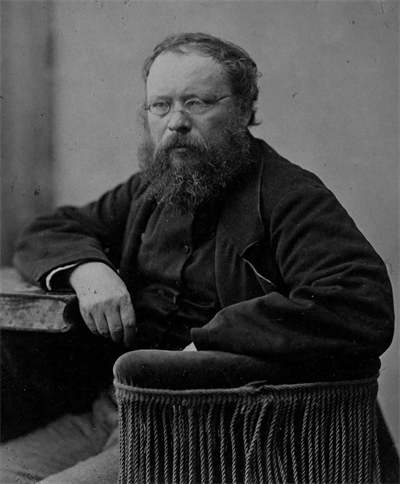本文譯自 Feenberg, A. (2010). Marxism and the critique of social rationality: from surplus value to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4(1), 37–49.
圖源 / 插畫家尼桑特·喬克西 (Nishant Choksi)
作者/安德魯·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
翻譯/陳榮鋼
我的標題表明,我有意將馬克思的著作與當前的技術問題聯系起來。我主要感興趣的是馬克思貢獻的方法論意義,而不是他思想的細節。同時,我還將觸及當代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t) 技術研究。為什么是馬克思?在當前的思想語境下,這個問題很合理,畢竟馬克思的經濟思想普遍被認為過時了,他的歷史意義也因蘇聯的垮臺而減弱。但馬克思與技術的交集仍有持續的影響,而且好幾方面的影響不會消失。
馬克思寫他的主要著作時,正值英國工業革命有望改變世界的年代。技術發展在人類歷史中的核心作用突然顯現。馬克思如何構想這場革命的作用?這個問題有很多爭議,而我關注其中一種闡釋。根據這種觀點,馬克思認為,技術取決于社會關系 (social relations) 。因此,技術必須從社會角度來理解,而不是把技術視作決定社會的因素。
這種觀點對任何技術的本體論闡釋都有影響,因為這種闡釋取決于更廣泛的社會本體論。我不會在這里直接進入本體論的討論,而是將重點放在其影響之一,也就是被視為內在社會現象的技術和知識之間的關系。
這種闡釋方法改變了我們對技術和知識的理解,并以一種新的方式開啟了政治問題。標準的觀點認為,雖然技術服務的目標由社會決定,但技術的設計取決于科學和技術知識的狀況。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的進步將技術拖在后面。
但馬克思在論證「工業技術的設計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的要求」時,似乎推翻了這個等式。知識在設計中仍然起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作用。相反,資本主義引入的制造業勞動分工導向了機器設計——將工人的任務分析和分解成簡單的零散的動作,為工作轉移到機器上做了準備。
馬克思預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將出現一種完全不同的勞動和技術分工。這些技術發展的思考意味著,生產所需的知識在現行經濟制度的影響下不斷發展,而現行經濟制度本身最終取決于階級權力。我將在本文的后面回到這個論點。
當代技術研究并非源于馬克思主義分析,而是與早期反實證主義 (anti-positivist) 科學研究的后續發展一脈相承。在庫恩 (Kuhn) 關于科學革命的名著之后,認識論的相對主義 (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 取得了勝利,因為科學被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現象來研究。在科學研究中,對實證主義 (positivism) 的摒棄為技術研究中與決定論 (determinism) 的決裂準備了條件。事實證明,技術也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不是普遍知識的工具性應用。建構主義旨在將我們從最后一個神話中解放出來——純理性的神話,其目的是打擊專家的獨裁主義。
《科學革命的結構》 托馬斯·庫恩
建構主義很幸運地在環境問題日益受到關注和互聯網興起的時刻出現。隨著公眾對技術的理解越來越復雜,對技術的學術研究找到了一個異常廣泛的受眾。然而,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復興喚起了人們對傳統理性主義的捍衛。啟蒙運動對迷信和不寬容的斗爭還沒有結束,仍然需要啟蒙運動的武器,其中包括對科學真理的堅定呼吁。討論的政治背景用現實的毒藥污染了知識空間,學術辯論走向了僵局。
我不打算在本文討論相對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哲學問題。我認為沒有必要解決這樣龐大的問題,不是非得這樣才能批判理性。我將論證,馬克思方法的某些方面為當前辯論中強調的認識論的替代方法指明了方向。把討論的背景擴大到馬克思,可能有助于我們把技術研究從它從科學研究的起源中繼承下來的沉重哲學負擔中解放出來。馬克思使我們能夠在理性的社會概念的框架內保持批判的立場。在我的結論中,我認為技術既是理性的,也是不確定的,它們共同建構了社會。因此,技術是政治性的,因為它的發展道路或多或少會受到辯論和選擇,其結果對構成社會的各個階級和群體的利益和生活方式都有影響。
我想首先將馬克思與福柯 (Foucault) 進行對比。福柯的思想可能是當今左派中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替代品。「權力/知識」(power / knowledge) 是福柯對理性治理的批判的關鍵術語,他將「權力/知識」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權力思想進行對比。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仍然將權力設想為「主權」(sovereign) ,也就是說,是壓抑性的 (repressive) 。在啟蒙運動中,真理高于政治的概念與此相伴。福柯聲稱,這些都是圍繞權力和知識的過時概念。
在現代社會中,知識與權力連在一起,它們一起產生了個人的主體性 (subjectivity) 和社會秩序 (social order) 。犯罪學和精神病學等學科與監禁機構一起出現,這些機構將人類對象置于它們的支配之下。它們通過懲戒程序重塑這些對象,從而創造了一個現代社會。
根據福柯的觀點,「權力/知識」是一個社會力量 (social forces) 和張力 (tensions) 的網絡,每個人都作為主體和客體被卷入其中。這個網絡圍繞著技術構建起來,其中一些技術在建筑或其他裝置中得以實現,還有一些則體現在標準化的 (standardised) 行為中。這些技術與其說是脅迫和壓抑個人,不如說是引導他們對自己的身體進行最有效的利用。在這種情況下,技術只是許多類似社會控制機制中的一種,所有這些機制都建立偽裝的中立知識之上,都對社會權力有不對稱的影響。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現代性 (modernity) 的社會要求被體驗為技術上的限制,而不是政治上的強制。監視、規訓權力、正常化 (normalisation) 等等,這些都使現代生活成為可能。它們在日常行為的層面上「濃縮」了技術和社會機能。最終,這些約束體現在結構中,決定個人的反射動作、技能和態度,比規則和命令更有效地決定個人行動。福柯談到「全景監獄」(Panopticon) 時寫道:
全景機制不是簡單的鉸鏈,不是權力機制和機能之間的節點。它是一種使權力關系在機能中發揮作用的方式,也是通過這些權力關系使機能發揮作用的方式。
《規訓與懲罰》
福柯聲稱,基于知識并嵌入社會技術和科技的權力不能被政治革命推翻。無論革命有多么猛烈,現代形式的國家通過「權力/知識」的影響而存在的,政策和人員的改變會使這些影響保持不變。福柯主張,在科學結構和方法的基礎上「顛覆性地重新安排權力關系」,以便整合那些處于等級制度底層的人所擁有的、被奴役的知識——目的不是要廢除權力,而是要找到一種方法,讓這些權力博弈發生在最低限度的支配下。
福柯的理論極具啟發性。重要的是,他不是通過攻擊科學本身,而是通過解構那些斷言「人類既是客體又是主體」的科學,來關注理性的支配形式。這些社會、政治、醫學和行政科學深深植根于現代社會的權力關系之中。破壞這種純潔性的主張,既為理解現代性提供了指導線索,也為知識領域新形式的政治抵抗提供了理論支持。所有這一切無疑是對馬克思的革新。但福柯并沒有對馬克思的觀點進行有效的整體批判。盡管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圍繞階級和國家的一些討論符合福柯的主權概念,但馬克思其實是第一個對社會理性進行有力批判的人。對于馬克思來說,理性的社會就像福柯一樣,受到權力的影響并產生偏見。
為了支持這一主張,我必須首先解釋我所說的「理性社會子系統」(rational social subsystem) 是什么意思,然后相應地修改「偏見」的概念。那么讓我從「社會理性」(social rationality) 的概念開始,我引入這個概念是為了明確許多現代制度的特殊性。
顯而易見,沒有任何制度能夠像科學和數學那樣具有完全相同的理性。制度不是通過邏輯關系,而是通過缺乏嚴謹的實驗和等式的因果和象征力量而維系在一起。然而,與科學和數學程序有一定相似之處的程序在現代社會中運作,對整個社會制度產生巨大影響。這種意義上的社會理性依賴于有意應用并在系統中制度化的三項原則——等價交換,規則的分類和應用,以及計劃結果的優化。
這些原則中的每一項看起來都是我們通常理解的「理性」。市場像計算一樣,是一種等價物的交換。官僚制度類似于科學,在某種規則下對客體進行分類和統一處理。而且像科學一樣,他們對客體的衡量也越來越仔細。商業像技術一樣,是基于優化的戰略。因此,我們時代的社會生活似乎反映了科學和技術程序。這對社會偏見的批評產生影響。
在歧視、情緒和各種偽事實影響了本應基于客觀標準的判斷時,我們通常就會看到偏見。我把這稱為「實質偏見」(substantive bias) ,因為它建立在信念之上,比如相信某些種族智力低下。這種「偏見」繼承了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目的是批判封建和宗教制度的敘事合法性。啟蒙運動呼吁,理性基礎、事實和理論不能受偏見影響。毫無疑問,啟蒙運動的批判在解放政治中發揮了作用,而且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啟蒙運動有一個重要的局限性,因為它暗示了技術、官僚制度和市場等系統的中立性和普遍性,這些系統聲稱有一個理性基礎。
要批判「市場」這樣的理性系統,就需要一個不同的「偏見」概念。為了解釋這個概念,我需要將它與浪漫主義的批判區分開來,后者將「實質偏見」歸于理性系統,從而否定了理性本身的合理性。在一些后現代主義、女權主義和科學技術與社會 (STS) 理論中也有類似的批判。但是,每當理性被簡化為非理性的起源(如西方或父權制的意識形態,或僅僅是權力關系),它作為理性的特殊性就被忽略了。
這并不是馬克思的方法。他在他那個時代的左派中也見過這種做法,比如在蒲魯東 (Proudhon) 那里,他把他最有名的書命名為《財產即盜竊」(Property Is Theft)。但是,如果財產真是盜竊,資本主義的條理與存在就不能被理解。任何社會秩序都不可能建立在簡單的掠奪之上,當然,像資本主義制度這樣復雜和脆弱的社會秩序也是如此。
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法國社會主義者、政治家、哲學家、經濟學家、互助主義哲學奠基人,首位自稱無政府主義者的人。
馬克思的獨特方法涉及一種非常不同的批判風格,基礎是我所謂的「形式偏見」(formal bias),批判理性秩序的歧視性影響。形式偏見隱藏在理性系統的各個角落,只有當這些系統被置于具體語境中時才會顯現出來。這不是一個偏見的問題,也不需要用偽事實或敘事神話來辯護,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系統本身就把歧視性原則客觀化了。批判被壓抑了,因為制度的捍衛者可以自證公允。例如,一項有文化偏見的測試可能會有效地區分不同的人群,但那些設計、管理和評分的人不需要自己帶有偏見就能得出有偏見的結果。
馬克思承認市場經濟的理性邏輯。但在1844年,他說:「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就越窮,這是一個當代經濟事實。」這個事實表明了市場的隱性偏見,馬克思著手將其解釋為資本主義理性結構的結果。這是一項困難的挑戰。哈貝馬斯 (Habermas) 簡潔地總結了馬克思面臨的問題:
市場制度承諾,交換關系總是因等價原則而實現公允。互惠原則現在成為生產和再生產領域本身的組織原則。
在這段話中,哈貝馬斯解釋了市場關系中數學上的對等性和道德上的對等性的驚人重合。正是這種等價性使市場合法化,并使它看起來既自然又良善。馬克思在他的剩余價值理論中超越了這種合法化。我在這里回顧他的論點,不是為了恢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是把它作為一個持續有效和有用的方法論例子。
在馬克思從資產階級前輩那里得到的資本主義經濟理想模型中,商品按其價值平均支付,其價值包括生產它們所需的勞動。勞動能力本身是一種商品,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以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來衡量。但是,由于資本家擁有工廠,他有權確定工作日的長度,而不考慮在其范圍內進行的勞動價值。在漫長的工作日里,工人生產的商品價值超過了他們的工資成本,因此他們使資本家致富,他們的產品屬于資本家。同時,工人自己仍然停留在只夠維持再生產其勞動能力的生存水平上。
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的這種批判中沒有提到偏見或偽事實。剩余價值由系統本身的理性運作而產生。財產不是盜竊,因為勞動是按其價值支付的。所以馬克思反對早期工會對公平工資的要求。問題不在于具體的工資率,而在于市場的結構,它使工作日的長度由資本家決定。然而,馬克思的論點確實有效地駁斥了市場的理性規范性 (normativity) 。當被視為一種純粹的等價物交換時,市場跳脫出它實際發揮剝削機制的背景。
我現在想談談馬克思的「形式偏見」概念和他對技術的批判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不是一個嚴格的技術決定論者,盡管他寫過一些著名的段落,他說「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系和所有的社會生活。他對技術的大部分具體討論涉及工業造成的傷害。這些段落似乎暗示了對技術本身的批判。但是,馬克思將問題歸咎于資本主義對機器的使用。也有一些段落批評技術具有資本主義特征。例如,馬克思寫道,科學「是鎮壓罷工的最有力武器,不利于工人階級對資本專制的周期性反抗」。「此外,還可以寫出一部自1830年以來的發明史,這些發明的唯一目的,是為資本提供反對工人階級叛亂的武器。」
安德魯·尤爾 (Andrew Ure, 1778-1857)
工業革命歷史上第一次觸及了上層社會成員的基本經濟生產。資本家擁有識字的技能和獲得科學知識的機會。同時,他們還接觸到下層人民所從事的手工業。他們對這兩個知識世界的熟悉使他們能夠重組勞動過程以消除昂貴手工業勞動。安德魯·尤爾 (Andrew Ure) 在1835年寫道:
出于人類本性的缺陷,工人越是熟練,就越容易變得任性和難以駕馭,在這個機械系統中,偶爾的不規則行為可能會對整個系統造成巨大的破壞。因此,現代制造商的宏偉目標是,通過資本和科學的結合,把工作人員的任務減少。
競爭推動了去技能化(deskilling,降低某工作的技能要求)的進程。但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具體社會關系,這就不是一種有效的經濟戰略。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受到上層極為縝密的控制,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至少就中央經濟制度而言是如此)。從上而下的控制使資本家在分工中處于一個全新的位置。資本家需要成為工作的統一者和領導者(不僅在政治上或經濟上,而且在技術上)。一旦勞動成為有償勞動,任務被分配,生產單位就不再具有準自然性質,這種性質植根于社群和家庭,并得到手工業行會及其傳統的支持。對于那些執行工作計劃的人來說,理解工作計劃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如果沒有資本家對「權力/知識」的行使,工人可能會通過放慢他們的步伐來抵制漫長的工作日,協調可能會崩潰。
但馬克思的分析更進一步,用福柯的話說,馬克思解釋了權力關系如何「在機能中發揮作用」。馬克思論述了去技能化導致的機械化 (mechanisation) 。一旦手工業工作被分解成最簡單的元素,并且每個元素在新的勞動分工中被分配給一個特定的工人,機器在執行工作中的潛在作用就變得很明顯。資本家的大部分作用可以在這種機器中得到客觀化。因此,資本需求主宰著工業革命,并帶來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的許多創新。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去技能化是各種發明的普遍特征,以至于它對經濟的逐步發展至關重要。但事實上,資本主義企業的歷史表明,在特殊的社會狀況和階級沖突中,去技能化的出現是多么偶然。讓人難以察覺的,是這些偶然所依賴的技術理性形式。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共有的、圍繞「進步」的舊觀念一直占上風。直到20世紀70年代,哈里·布拉弗曼 (Harry Braverman) 的開創性著作《壟斷資本主義中的勞動」(Labor in Monopoly Capitalism) 才在重提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時談到了去技能化的概念。
隨后,大衛·諾布爾 (David Noble) 對美國工業化中去技能化的作用進行了有力的研究。諾布爾談到機床行業自動化的著名例子。他解釋說,機床可以通過兩種不同的方式實現自動化。起初,通用電氣公司 (GE) 引進了一種模擬錄像/回放系統,但它沒有找到買家。管理層堅持認為,數字系統可以直接從工程圖紙轉化為機器運動,完全將手工業者排除在外。諾布爾的論點體現了建構主義者所說的「不充分的決定性」(under-determination) 。管理層在這些系統中的選擇最終取決于他們對手工業勞動的意識形態敵意,而這種敵意得到了管理科學的長期支持,而不是取決于「中立的技術」或經濟原因。
這種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有助于將馬克思主義者從「將技術進步視為普遍成就」的天真觀點中解放出來。根據新的闡釋方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彼此共同建構 (co-construction) 。「共同構建」屬于最新的建構主義技術研究,它重新發掘了馬克思關于社會和技術相互依存的思想。因此,當代技術研究提供了一些概念,有助于分析這些變化及其背后隱藏的東西。
在這一領域,技術不被設想為發明天才的純粹產品或科學應用,而是被設想為社會行動者 (social actor) 的「建構」。人造物 (artifacts) 的技術決定性不充分,為社會在不同設計之間的選擇留下了空間,這些設計有重疊的部分,能更好地服務于某種社會利益。這意味著,語境不僅僅位于技術的外部,而且滲透到了技術的合理性中,將社會需求帶入齒輪和杠桿、電路和燃燒室的工作中。
在一篇頗有影響力的文章中,特雷沃·平奇 (Trevor Pinch) 和維貝·比克 (Wiebe Bijker) 將科學研究中的建構主義與技術的平行方法聯系在一起。他們用自行車的歷史來說明他們的論點。正如諾布爾的機床例子一樣,起初有兩種主要的設計在競爭。其中一個設計看起來很像今天的自行車。它騎起來相對安全,但速度很慢,只作為一種運輸工具使用。另一種有一個高大的前輪,速度更快,但穩定性較差,它吸引了那些喜歡比賽的年輕運動員。因此,不同設計符合不同社會主體的要求。低輪車的勝利是因為引入了充氣輪胎,以減少振動。當這些輪胎被用于自行車比賽時,低輪車被證明快速而穩定,并很快成為首選設計。
平奇和比克主要研究社會對「人造物本身的內容」的影響,而不僅僅是對使用或發展速度等外部因素的影響。這似乎與科學研究中類似的建構相對主義 (constructivist relativism) 并行不悖,但這種并行在一定程度上有誤導性。事實和人造物是完全不同的。通過實驗和復制來「硬化」(hardening) 自然科學事實所產生的「內容」遠比成功的技術設計更引人注目。當然,工程學的要素通常由科學方法和長期的經驗建立起來,但是它們離「成品」還有很大的距離。在這個過程中,技術的闡釋靈活性就顯現出來了。對于技術專家來說,成品的「不充分的決定性」是激進的技術。它的論證不需要微妙的認識論證據。福柯謹慎地將自己的研究限制在精神病學和犯罪學等科學領域,這反映了他對這些學科同樣「軟」地位的欣賞。
「辦公桌上的競賽」清楚表明,技術產品的社會建構是對用戶生活的干預。銘刻在人造物中的「腳本」(scripts) 支配著它們的使用,從而支配著社會行為的很大一部分,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支配著用戶的生活方式。用戶由人造物構造著,但反過來又影響了它們的設計。在技術傳播過程中進行的互動既塑造了人類,也塑造了技術本身。
技術的新問題不是關于效率 (efficiency) ,而是關于意義 (meaning) 。技術有兩方面的理論。技術的性質不能簡化為兩方面其中的某一面,要么涉及它的因果關系系統,要么涉及它建立的意義背景。這兩個方面是同源的 (equiprimordial) ,只有在對任何具體技術的正確理解中才有分析性的區分。任何技術本體論都必須從這種原始的二元性出發。
從這個角度看,馬克思主義者分析的去技術化的歷史是對工作和工人兩種不同看法之間的闡釋學「競賽」,一種由資本推動,另一種由工人推動。去技術化要在工廠設備的技術規格中實現資本主義對工作的闡釋,于是一種新型的社會是圍繞著這種轉變而建立起來。
我提出「技術編碼」(technical code)這個術語,指的是在社會行動者的語言和當時的技術語言之間翻譯這些意義的一般規則。我們被這樣的技術編碼包圍著。環保主義者對氣候變化的關注被轉化為發動機和建筑規范的規格。對汽車工程師來說,安全是安全帶、安全氣囊、電子防滑控制系統 (ESC),等等。
在布魯諾·拉圖爾 (Bruno Latour) 的詞匯中,每一種語言都被用來動員不同的網絡。普通語言動員了人類行動者,包括普通民眾和政治領導人。在這些被動員的人中,有技術專家,他們的技術話語動員了非人類的行動者,以執行對抗氣候變化或建造更安全的汽車等計劃。枯燥的工作是一種技術編碼,一方面以話語形式表現為「用機器取代熟練勞動力」的意識形態偏好,另一方面表現為確定具有該功能的機器技術規格。資本主義的技術編碼將上面的控制要求轉化為技術。
馬克思暗示過社會主義技術編碼的可能性,它將解放智力和技能。例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 中,馬克思寫道,社會主義下的勞動必須:
「具有科學性,同時又具有普遍性,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訓練出來的自然力,而是一個主體,這種主體不是以純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而是作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種活動出現在生產過程中」,這就是主體的創造性勞動,是「主體的物化」,是個人目的「自我實現」,也就是自由的真正實現。
(人民出版社譯本,1980年)
「具有科學性,同時又具有普遍性,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訓練出來的自然力,而是一個主體,這種主體不是以純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而是作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種活動出現在生產過程中」,這就是主體的創造性勞動,是「主體的物化」,是個人目的「自我實現」,也就是自由的真正實現。(人民出版社譯本,1980年)
現在,我想談談近代技術批判政治學的發展。我試圖說明,馬克思預見到了福柯的基本觀點,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必須把理性包含在內。工資勞動和技術的結構正需要這樣的批判。但這些制度不再像馬克思時代那樣局限于資本主義企業。在20世紀,它們擴散到國家機構,并最終傳播到共產主義社會。由此可見,工人運動只不過是一種更普遍的技術政治的初始實例。技術被廣泛應用的第一個地方是工廠,因此技術抵抗首先在那里顯現出來。一旦技術傳播到社會的整個表面,就會出現更廣泛的技術斗爭,從當代環境、醫學和計算機化的政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斗爭場景的增多表明,技術理性的偏見不基于所有權 (ownership) ,而是基于我所說的「資本家及其行政繼任者的經營自主權」。我所說的經營自主權,是指所有者或經理不顧下屬行動者和周圍社群的意見或利益,作出獨立決定的自由。經營自主權將管理置于與世界的技術關系之中,使其不受自身行為的后果影響。它能夠在它選擇和命令的技術的每一次迭代中再生產它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技術官僚制是這種制度向整個社會的延伸,以響應技術和管理向社會生活各個部門的擴散。于是,一種自我延續的動力出現了。我們可以采用托馬斯·休斯 (Thomas Hughes) 的術語,稱之為現代組織在擴張和發展過程中獲得的一種「勢頭」(momentum,或譯作「動量」)。
不幸的是,社會主義運動仍然固守在「所有權」的概念上,并期望在沒有技術關系民主化的情況下從國有化 (nationalisations) 中創造奇跡。技術的中立性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教條,就像它成為資本家的教條一樣,并且直接拿來用,使最具壓迫性的西方技術設計構成了蘇聯工業化的基礎。由于未能將經營自主權問題置于轉型理論的中心,導致俄羅斯、中國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出現了災難性的權力集中。到20世紀70年代,這種方法在西方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已經失去了信譽。勞動過程理論和各種形式的新馬克思主義開始用更復雜的路徑理解馬克思的社會理論,在某些方面與福柯的非馬克思主義理性批判并行不悖。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修正馬克思主義對整個現代文明進行了激進的批判。這一趨勢的最著名代表是馬爾庫塞 (Herbert Marcuse) 。他提出了現在已經成為陳詞濫調的復雜批判論點——通過媒體宣傳、技術官僚意識形態、私有化、消費主義以及將過剩的侵略性轉移到種族或外國的替罪羊身上,使「單向度的」(one-dimensional) 系統穩定下來。
此外,馬爾庫塞以對技術理性的激進批判挑戰了對「進步」的盲目信仰。在主流意識形態中,技術被視為對自然知識的純粹應用,超越了政治和社會差異。技術的理性特征是它的「不在場證明」,使它擺脫了責任,并使它超越了爭論。馬爾庫塞對這種號稱中立、不偏不倚的技術形象提出質疑。他認為,技術的「中立性」注定它要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服務。因此,現代技術與傳統工藝不同,因為傳統工藝被束縛在特定的、有文化保障的價值的服務中。如今,技術從文化中解放出來,使它可以用于任何用途。
馬爾庫塞不太關心福柯關注的權威 (authority) 問題,而是關注科學技術理性在現代社會中發展的先天局限性。他的論點重現了浪漫主義理性批判的某些主題,比如對量化 (quantification) 的懷疑(以政治形式出現)。馬爾庫塞將統治的科學和技術與尊重自然和人類發展潛力的另一種理性進行了對比。馬爾庫塞認為,這樣的替代方案將植根于對世界的想象性理解和對美的感受。馬爾庫塞的狂喜在今天聽起來是不可思議的烏托邦,但它提出了一種非常不同的技術未來之愿景,如果我們要看到充分應對環境危機所需的根本變化,就需要有某種愿景。
馬爾庫塞的影響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高潮,當時的反文化態勢要與美國的生活方式徹底決裂。這時的活動家們呼吁以商品以外的形式去追求幸福。馬爾庫塞對消費主義批判非常重要,他拒絕否定個人自我,而是強調,我們有必要重組系統的技術基礎。他認為,塑造現代技術的文明事業可以被另一種基于尊重自然的技術所取代。反文化的消失并沒有駁斥這一信息。為了當代的目的,馬爾庫塞的論點可以被重新表述為技術的「不充分的決定性」,這為另類現代性提供了可能。
這一歷史背景解釋了實證理性主義和技術官僚決定論的衰落。二戰后,這些思想霸權在英語世界取得了勝利。新左派及其反文化的突然出現侵蝕了戰后的霸權確定性。理性不再是一個,而是多個——至少在具體社會中是這樣,因此受制于政治,而不能以某個統一真理的名義推翻它。
理性的改變解釋了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技術社會研究。到20世紀末,對技術的學術研究已經放棄了決定論和工具論,而選擇了各種建構主義的替代方案。我們看到,這種技術批判的去政治化 (depoliticised) 提出了重要的方法創新。但是,建構主義社會科學在研究自身時卻受到了明顯的抑制。這種抑制無疑解釋了所謂「科學戰爭」的沖擊。在這場戰爭中,典型的實證主義和技術官僚論調面臨著建構主義者的挑戰。當攻擊來自左派時,風險就更大了,因為左派是大多數建構主義學者的「天然家園」。比方說,米拉·南達 (Meera Nanda) 認為,后現代主義和建構主義被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操縱。她寫道:
新印度教和印度教是反動的現代主義運動,意圖利用無意識的、甚至是危險的技術現代化來推進傳統主義的、極度反世俗的和不自由的社會議程。然而,他們都共享一種后現代主義的科學哲學,贊美那種被稱為「吠陀科學」(Vedic science) 的科學、精神、神秘主義和純迷信的矛盾混合體。
建構主義者顯然沒有想到,雖然他們的理論可能會破壞技術決定論,但對原教旨主義卻毫無用處。如果把科學和技術等同起來 (technoscience) ,這個問題將變得無解。除非科學和技術被區分開來,否則就無法避免進步的、民主的、反對原教旨主義的主觀偏見和反對技術決定論的形式偏見之間的矛盾。科學技術和社會研究起初并不愿意明確提出反技術官僚的論點,正如女權主義批評家指出,維貝·比克「在學術上迂回」,已經遠離了主要的政治道路。
如果這個話題繼續下去,技術研究和政治理論的相遇可能會帶來社會科學的重大重構。拉圖爾認為,將技術排除在社會科學的社會概念之外是站不住腳的。但是,一旦技術進場,那么理性的問題就會以新的面目出現。韋伯 (Max Weber) 引入了理性化的概念來解釋馬克思早先提出的「現代性的眾多核心進程」。但在馬克思那里,這些進程被設想為潛在的多重性。韋伯認為,它們對所有現代社會都是一樣的(無論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在,基于技術的新興問題意識,我們有了質疑韋伯簡化論調的基礎。理性化必須觸及社會的多重性。技術發展沒有單一的同質化結果,因此社會發展也沒有。社會科學的確定性和封閉性被重新打開,而民主化的問題關乎社會對發展的影響將以何種形式在理性化的領域中被行使和制度化。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