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所稱的城市秩序,主要指的是18世紀末期以來在全球發端的近代型和現代型城市的秩序問題。城市隨著工業體系的擴張而擴容,城市數量增多,城市中的新形態增加,城市空間擴大但留給每個人的空間縮小。

最早具備資本主義工業秩序的城市出現在英國,比如曼徹斯特。恩格斯在其城市史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書中就記述了當時的曼徹斯特為代表的英國工業城市的結構,展現了工業革命以后工人階級陷入最為糟糕的生活和勞動狀況。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城市化創造了工人階級。托克維爾等人則給出了立場相反,但判斷一致的看法。城市“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產生之地,也是矛盾被發現和被解決的場所……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堪為經濟變化的熔爐,堪為社會沖突的舞臺”。
社會階級思維與城市秩序 城市秩序不可能擺脫饑社會階級思維。在歐洲,工人階級被資本主義城市化催生,哪怕在工人運動在20世紀后期逐漸式微以后,仍然表現出相對意義上的團結一致性。而在美國,這一催生進程離奇地因19世紀歐洲移民潮打斷,從而使得人種和種族的政治活動超越了階級身份的界限。
當然,正如新出版的《城市秩序:城市、文化與權利導論》一書中所談到的那樣,后現代城市最核心的一點特質就是重新詮釋了城市,將一些原本很合理界定為階級矛盾的問題被描述為純粹的城市規劃理念的問題,比如城市街區逐漸變得更為給封閉,將入口隱蔽起來,切斷本區域住戶與其他居民的來往。這些街區的公共建筑也被封閉起來。這表現了城市居民對于他者所心懷的恐懼。這類問題如果在20世紀中期以前,將很容易被界定為社會階級問題,但現在不然,甚至很可能不被認為存在任何程度上的不當。

城市秩序之中一些被認為是典型的經濟問題,實際上也完全可以用社會階級思維加以解析。比如首位型城市等級體系,也就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省份,居于首位的城市占據絕大多數或較大份額的發展項目、資源、人口,并不斷吸走其他地區的資本和服務功能,帶來經濟增長的分布極端不平衡。英國就是典型的首位型城市等級體系。而美國城市為代表的城市等級體系可以被認為是標準型城市等級體系,這使得各地的城市規模和數量都在持續增長,當然,也有部分地區因傳統制造業衰退而陷入衰落。還有一種城市等級體系呈現混合型特征(如澳大利亞)。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發展,出現的共同特征在于:知識經濟的發展、勞動市場上雇傭的臨時化、顯著的貧富生活水平分化。過去,城市研究專家將城市分為生產型城市和信息型城市,認為后者更可能擁有相對公平的社會分工,但事實上并不是這樣,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在全球價值鏈任何位置上的產業和城市,都必然會創設出機制來降低勞動力成本。但同時,這些產業和城市,又希望人們拿出更多的錢來消費和體驗,甚至創造出“支持和鼓勵持續消費的意識形態”,以及消費金融體系——這兩者之間的尖銳張力,是如此清晰可見。
資本、勞動與城市 《城市秩序:城市、文化與權利導論》這本書以發生在澳大利亞悉尼的城市建筑工人、行業組織與資本的博弈案例,探討了資本、勞動與城市的互動關系。悉尼等城市在20世紀60-70年代經歷了一輪城市化擴張浪潮,商業寫字樓和住宅擴張,由此出現了房地產繁榮,也意味著房地產業吸納了相比之前更多的勞動就業。這一轉變也增強了當地建筑工人相較于開發商的博弈地位,爭取改善勞動環境,增加薪資待遇。但這種努力被悉尼主流媒體抹黑為目無法紀,認為是流氓主義行徑。工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迎來了勝利,開發商為了避免工期延誤而不得不增加了福利配置。
悉尼本地居民與開發商矛盾凸顯以后,標志著事件進入了第二個階段:房地產繁榮并不意味著所有本地居民受益,比如新建樓盤增加,就會降低舊房屋的售價和租金吸引力,而且新樓盤會導致本地人的公共空間受侵蝕,還得忍受越來越擁堵的交通。當地建筑工人與本地居民權益組織結盟,從而化解了此前持續受到的妖魔化評價。

盡管20世紀70年代以后,悉尼的房地產繁榮周期結束,但勞動保護政策并沒有回到之前的狀態,而且民眾、勞工彼此之間的團結也沒有被破壞。
不斷流失和新涌現的工作 另一個案例更具代表性,也就是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20世紀后期開始就不斷流失原本位于城市城區或郊區的制造業崗位,這些國家的城市產業開始被置換為更為高端、專業性的服務業。以英國為例,1971-1981年,男性從事的工作消失了170萬個,雖然女性就業崗位增加了150萬個,但這一增一減之間,減少的是擁有完善勞動福利的正式崗位,而增加的卻多是服務業外包崗位。這種情況下,英國等國家誕生出所謂的“雅皮士”(不斷向上流動的年輕人)、雅廢士(不斷遭受挫敗的年輕人)的概念,而后者的數量遠遠多于前者。
實際上,歐美國家之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致力于削減社會福利,就在于雅廢士群體數量的增加,所以通過削減社會福利,又沒有完全取消,降低社會動蕩,但又要促使(逼迫)領取者不喪失尋找工作的動力。然而,正如《城市秩序:城市、文化與權力導論》書中所提到的那樣,美國、英國等國家20世紀后期消失以及新增的崗位,存在性別上、勞動性質上的高度不一致,還有技術類型的高度不一致。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首先富裕起來的城市,新涌現的工作,主要是金融服務業,這是原先制造業勞動力所不可能勝任的行業。新興行業、勞動者替代過去的行業、勞動者成為了城市空間的主宰者,促使城市空間進行了調整,商業空間急劇擴張,住房空間進行了空間上的轉換,受此影響,樓市經濟滋養了上述國家和城市的經濟增長。相關的項目通過高度金融化的運作,從而更快地改寫了相關城市的經濟地理。
這種情況下,城市歡迎雅皮士,并為之定制鼓勵基調的意識形態,而對雅廢士這一階層抱以高度警惕,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城市街區開始變得越來越封閉的重要原因。
更加隱蔽但并未消失的階級斗爭 城市階級斗爭并未消失,但相較20世紀前期以前確實變得更加平淡。一個簡單的理由,那就是因為住房經由城市運作變得昂貴,很大一部分中產階級以及中下階級都受困于房貸,這使之必須進行心理建設來服從現有秩序。
但正如《城市秩序:城市、文化與權力導論》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城市的住房市場每時每刻都處于變化的進程中,質量惡化、投資流失、質量進一步惡化的向下螺旋會讓街區以及相當數量的民眾陷入越來越糟糕的困境。而且,美國等國家的城市更新、房地產運作總是呈現這樣的特點:
被拆毀的住房比修建的多;被拆毀的主要是低租金的住房,修建的事主要是高租金的住房;住房條件最糟糕的人群的住房條件惡化;住房條件最好的人群的住房條件得到改善。
自然,在美國以及其他一些以美國為標桿的國家,很多人甚至大多數人會將自己定義為中產階級,并由此被偏自由派或偏保守右翼的意識形態所俘獲。實際上,哪怕是從事信息產業的中產階級,本質上仍然屬于與資本對立的勞動階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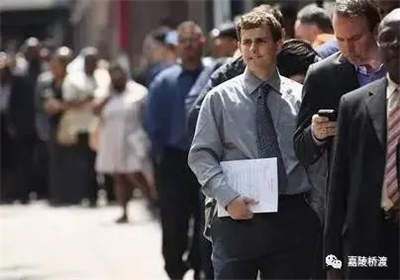
很多國家,哪怕是美國、英國、日本,都存在相當旺盛的非正規經濟,包括但不限于零售、小規模運輸、個人服務、安全保衛、廢品回收、乞討以及其他非法生意。我們所說的擺攤經濟,也是非正規經濟的一種。還有所謂的社區互助經濟,也就是商品和服務非現金交易,尤其是在工人階級街區,這類交易方式非常普遍。一些記者、文學家對社區互助經濟給予了溫情脈脈的描述,但實際上,這只不過是社會和經濟競爭中的失利者通過加強互助來避免防止更快、更深下滑的努力,而且常常以失敗而告終。
書中還談到了日漸增強了對所在國以及城市影響力的工商企業。指出這類企業非常精明地通過自己的投資或撤資的行為來干預城市的經濟和政治生活,其訴求無非是稅收條款、勞動保障條款和環境保護條款的相對松動。“工商企業都希望有一個能容許自己凌駕在勞動力之上的立法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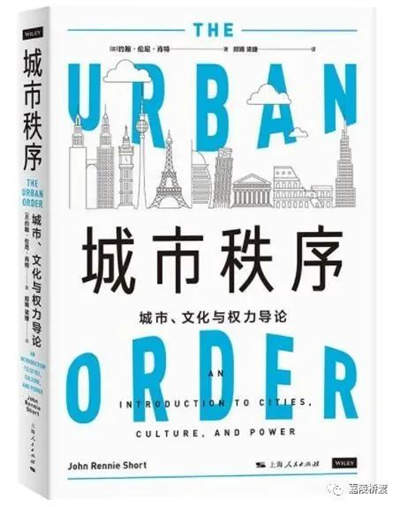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