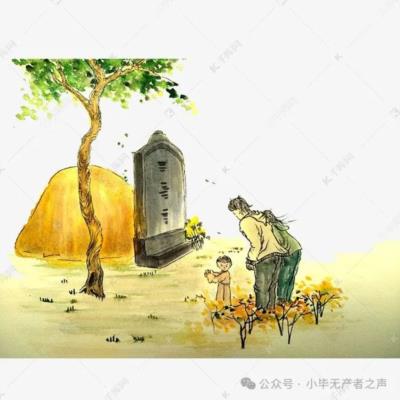明天是清明節,是中國人習俗上上墳的日子。
我現在就在老家,準備明天和親人去給過世的老人上墳,這些年,長輩走的越來越多,于是越發覺得上墳是重要的,以前上的是從未見過的人的墳,感覺無聊,還嫌鞭炮聲入耳太吵,現在地下長眠著曾經同甘共苦的親人,那是無法再一見,無法再擁抱的親人,便開始理解上墳,把上墳當成了自己該做的事情。
所有人一生,都有一遺憾,就是摯愛的親人,在他生前,我們任性了,和他們沖撞,在他們走后才想起,對著空蕩蕩的屋子無計可施,我想起以前我偷手機玩被我姥姥發現了,就生氣的沖她發火,怪她讓我玩不成手機,現在每想起,都覺此事尚未道歉,內心無比遺憾。
上墳是中國的傳統,以前掌握在統治階級手里,因而表現出如魯迅筆下《祝福》一般的迷信和壓迫性質,而在社會主義中,上墳絕不是無意義的,但是應以符合勞動人民需要的形式上墳
明天我要去給我故去的親人上墳,我不知道去做這件事情究竟為了什么,我能想到所燒的黃紙和冥幣是不會有地下的親人收到的,死了就是死了,可我還是要去上墳,我只是冥冥的感到這是有意義的,是什么意義,我卻一個字都說不上來,這真沒法不讓人聯想到海德格爾和薩特的哲學,上墳這件事的的確確是講不出意義的,但這意義并不是沒有,只是不可說,上墳是個生死之事,整個宇宙和生死相比都是渺小的事情,更何況我們相比宇宙,只是一粒微塵。
馬克思主義者不信有鬼神,這是對的,可是如果僅僅因為人死后沒有鬼魂,就認為不該上墳,那這種認識還不是辯證法,更不是唯物主義,人的情感的需要是一種物質,如果說宗教儒學,對上帝,對天地君親的崇拜是一種作為統治階級需要的精神物質的話,那么對故去親人的追思,應該是一種人生來的,正當的精神物質,上墳恰恰是這種精神需要在現實世界的滿足。
我們的親人死后,我們仍然不允許別人在背后抹黑他們,這說明人死后,他仍然是需要意義的,他仍然是應有作為人的尊嚴的,而與朋友,親人的交往同樣是一種尊嚴,在親人死后,繼續去看望他們,去上墳,不僅僅是滿足我們生者的精神需要,更是象征著已死的親人還有作為人的尊嚴。
死后無人記得,有限之人生成漫長時間之一瞬,是一種悲哀,祭祀恰是為了使死者不受漫長時間的羞辱,賦予有限人生之無限性的哲學期望,絕不是如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理解的“封建迷信”
當然,上墳不必定死在清明,清明有事,也可以換個日子,可是墳總是該上的,找個不麻煩的日子,紙燒一點,鞭放一點,形式走一點,不必貪多,在墳前坐坐,和親人傾訴這些年的生活,這就足夠了。
有人說,能不能取締形式,不燒紙,不放鞭,但是要我說,這種形式是有意義的,燒紙和放鞭等等習俗,本質上是符號,而這些在場的符號客觀上,攜帶著不在場的紀念親人的意義,就好比我們所說的過年的鞭炮和春聯攜帶著年味一樣,上墳的形式是追思的行為的聚合軸,是上墳作為符號表達紀念意義的必要的要素,形式可以從簡,但是不能取締。
有些男的死保守,不讓女人大年初一去上墳,說這是“傳統”,咋?年初一這天就男人有祖先,女人不配有祖先嗎?我看男女都講一個上墳平等,都有平等的追憶祖先的權利。
恰恰是父權制度,催生了男性上墳的特權,更賦予了“生男”必要性,因而上墳這一人類都需要的精神需求和男性捆綁在一起,只要男性對上墳的特權存在一日,那么私有的,攀比異化的上墳亂象就會一直存在
現在上墳還是一個私有化的事情,是“各人自掃門前雪”,只上自家的墳,我想以后應該組織公共上墳,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是公有制度下的社會主義建設者,死后就該公葬,表彰他們生前為社會主義所做的貢獻,以后的祭拜就和烈士陵園一樣,每年組織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們公祭,烈士們為國捐軀,是保衛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做貢獻,而解放了的勞動者為建設社會主義奉獻自己的青春,同樣是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死后也應該享受社會主義國家的公祭。
清明來了,大家也別都自掃門前雪,我也倡議大家有時間的話去烈士陵園走走,獻花就不必了,我不希望有人把對烈士的追思物化成一朵作為商品的空洞洞的“花”。
有人說:怎么你說燒紙就是符號,這獻花就不算了嗎?我可以說,烈士公祭上墳,自有公共組織,我們普通人買花,豈不是越俎代庖,花這個符號是一定有的,對我們紀念烈士的普通人而言,重要的是我們要發自內心的懷念,而不是把符號異化于追思本身之上。
燒紙、鞭炮、獻花都是上墳的儀式,也是攜帶著追思意義的符號,但是符號本身依然是符號,我們所尋求的是追思故人的精神,而不能讓符號異化成為上墳的主宰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