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的深層歷史構(gòu)境
此文的主體內(nèi)容乃拙著《保衛(wèi)<資本論>——經(jīng)濟形態(tài)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17)之尾論(作為總結(jié)性的一章)。此次根據(jù)發(fā)表需要,對該章文稿結(jié)合全書主題,進行了有針對性壓縮和改編,得以采用恰當?shù)男问胶妥x者見面。魯迅先生有言:“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錢鐘書先生則強調(diào):“對癥亦知須藥換,出新何術(shù)得陳推。”其闡明中國政治經(jīng)濟學(xué)遠航方法論路徑,遂為中國經(jīng)濟學(xué)研究“導(dǎo)論”意義之作品。又由于洞悉了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遂完成最為深遠意義之政治和經(jīng)濟的“歷史組裝”工作。然則,由于“中國經(jīng)濟學(xué)建構(gòu)”行動使命,研究固然還局限在方法論層面上,但實質(zhì)內(nèi)容已提出“重新研究全部歷史”之工作要求,乃至可能成為推動我們的理論向深處進軍之研究綱領(lǐng)。謹以此文紀念偉人馬克思誕辰200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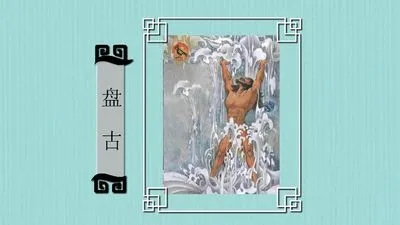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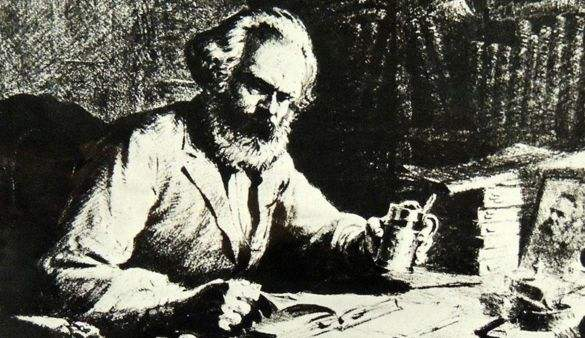
一、《保衛(wèi)<資本論> 》工作意蘊解析
《資本論》始終是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研究的一塊基石。月移花影約重來,我國業(yè)已掀起的“熱研《資本論》”浪潮,其中最有價值的一點恐怕就是:通過還原馬克思的學(xué)術(shù)精神,深度挖掘《資本論》的科學(xué)品質(zhì)與藝術(shù)涵養(yǎng),以達到“為我所用”之目的;同時又由于中國方法、中國智慧、中國學(xué)科,這些“中國元素”最大程度地集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原創(chuàng)性內(nèi)涵,可以深切感受到此項工作所實現(xiàn)者“經(jīng)濟學(xué)的回家,回歷史,回中國”也!此為具有民族蘊涵特征之“學(xué)術(shù)坐標系”研究升級。【注:此“頂層設(shè)計”是大象無形的,體現(xiàn)“行動的科學(xué)”和“歷史的科學(xué)”的合一性要求,促使“研究”和“敘述”必須作為“實踐態(tài)的思維”予以考察。拙文“我為什么與如何寫《保衛(wèi)》”將之概括為:“整體看,這是對《資本邏》予以‘保衛(wèi)’的學(xué)術(shù)價值、工作意義和建設(shè)路徑。”(《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報》2015年第4卷)】
故此,可認為,《資本論》的深層境界在于構(gòu)筑了“客體批判”的歷史科學(xué),完成以副標題對主標題的系統(tǒng)性書寫。【注:主標題是學(xué)科對象和研究對象,副標題是學(xué)科方法和工作邏輯;主標題體現(xiàn)的是對“天人合一”的社會歷史背離,副標題是體現(xiàn)的是對“知行合一”工作理念的回歸。因此,《資本論》可以視為“客體批判的抽象力”。蓋因其“認定抽象力是優(yōu)先作為研究規(guī)定,指示主體行動力”,以“實踐化的知識”切入行動理論,從而生成“辯證法的實踐態(tài)”。(參閱許光偉等:《馬克思“抽象力”理論規(guī)定本根與溯源——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中國經(jīng)濟問題》2018年第4期)】

進而,《資本論》實現(xiàn)了以批判為“學(xué)科方法”宏構(gòu)社會發(fā)展理論,以致,以發(fā)展為批判的工作指向性將“批判”設(shè)定為發(fā)展規(guī)定之中心內(nèi)容,奠基大寫字母“批判科學(xué)”方法論。大道至簡,我手寫我心,“新時代”的中國理論構(gòu)建行動亦需要適時地從“黃昏時分”起飛!簡言之,這是有關(guān)于“中國主體批判”之深層歷史構(gòu)境。
行動議程包括:(1)突破單一路線的批判研究,實現(xiàn)“主客體批判”并舉;(2)以總體研究方法和思維把握“身份二重性”與“勞動二重性”之歷史共生;(3)以“貫通”之法形成對產(chǎn)品和商品經(jīng)濟形態(tài)“相互拱衛(wèi)”之全方位、系統(tǒng)研究;(4)以《資本論》為“體”踐行和弘揚“中國行動規(guī)定”,強調(diào)“主體批判”的工作領(lǐng)銜為中華體系所獨有,等等。總的來講,以上研究表明:通過“中國人資格”的閱讀和研究工作成分的介入,《資本論》依然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召力,此為“學(xué)術(shù)保衛(wèi)”之指向性,意味著對中西方學(xué)術(shù)工作關(guān)系的“重構(gòu)”;并且整體看,這不啻又是一次“人類智慧革命”,昭示文明規(guī)劃新圖景,所以惟其強有力,必能推動理論研究向深處進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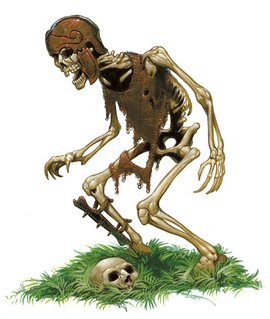
二、中國經(jīng)濟學(xué)研究:從“主體批判”啟航
關(guān)于中國經(jīng)濟學(xué)的研究起點,學(xué)界爭論很大。而對《資本論》和西方主流經(jīng)濟學(xué)的“洋教條”的推崇,也極大地制約了對中國歷史的思考。“既然《資本論》俄國化,不是爬行資本主義道路,因而也就不能將《資本論》中的概念范疇抄襲到俄國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同樣道理,《資本論》中國化,也不是中國爬行資本主義道路。因此,中國同志也不能將《資本論》中的概念范疇移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jīng)濟學(xué)。”但是,“在中國經(jīng)濟學(xué)理論界,肅清教條主義的任務(wù)仍然繁重而艱巨。中國經(jīng)濟學(xué)界一批又一批的經(jīng)濟學(xué)家,一直試圖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把《資本論》中的概念范疇生搬硬套到社會主義經(jīng)濟之中。”【注:丁堡駿:《論俄國化與中國化(下)——兼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zhì)》,《當代經(jīng)濟研究》2018年第6期】
關(guān)鍵是如何把握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發(fā)生學(xué)和系統(tǒng)發(fā)生學(xué)。用一勞永逸的“一般歷史哲學(xué)”是永遠也得不到正確答案的。關(guān)于《資本論》的“俄國化”,丁堡駿教授指出:“當時俄國所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和矛盾,不僅僅是俄國自己國內(nèi)的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矛盾的反映,而且同時也是當時歐美國家的社會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矛盾的體現(xiàn)。這就印證了馬克思將落后國家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生產(chǎn)方式,是與西歐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同時代的東西,它就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結(jié)論。”從而確證:“俄國的經(jīng)濟事實根本不是這樣,俄國公社并沒有完全解體。俄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chǎn)力水平也遠沒有發(fā)展到足以促使資本主義滅亡的高度。”然則,“馬克思經(jīng)過對俄國特殊社會歷史條件的分析得出結(jié)論:俄國農(nóng)村公社完全可以不經(jīng)過爬行英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道路,可以不走歐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道路,徑直走進歐美資本主義也必將要走入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注:丁堡駿:《論俄國化與中國化(中)——兼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zhì)》,《當代經(jīng)濟研究》2018年第6期】
要之,是認識到,“馬克思之規(guī)律論又是一個‘弱’規(guī)律論,而不是‘強’規(guī)律論,因為深得辯證法精髓的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社會形態(tài)是一個復(fù)雜的‘有機體系統(tǒng)’,社會發(fā)展中‘現(xiàn)實的人’具有主體作用,必然性通過偶然性得以顯現(xiàn),社會規(guī)律具有‘似’(‘相似’而‘不是’)自然規(guī)律的特征。”【注:聶錦芳:《馬克思為什么沒有完成的定稿工作——紀念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中華讀書報》2017年9月6日第9版】
歸根結(jié)底,“教條主義在方法論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因此,盡管它所搬弄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xué)理論,但是它本質(zhì)上仍然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或反馬克思主義的。”【注:丁堡駿:《論俄國化與中國化(下)——兼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zhì)》,《當代經(jīng)濟研究》2018年第6期】
必須審視“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在批判工作中的重大意蘊。書寫歷史,要在顯露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的全部工作邏輯。馬克思偉大而不足,是相對“中國原創(chuàng)”而言的。要之,主體批判與客體批判在規(guī)定上“和而不同”,它們社會對立而歷史貫通。相對來說,主體批判整體上體現(xiàn)了中國歷史之“原創(chuàng)”。于是,只有使中國原創(chuàng)和馬克思原創(chuàng)內(nèi)在對接,方能明了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真正的學(xué)科涵義。鑒于資產(chǎn)階級經(jīng)濟學(xué)對“知識邏輯”的高度推崇,我們必欲從方法論與理論層面進行撥亂反正!從而必須深刻認識到,批判的二重性作為“抽象力”乃是總體思維之“總起”。
亦即,從整全的批判規(guī)定出發(fā),在這一語義項下,必須認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一樣古老”之理念,建立雙重發(fā)展追索認知:物質(zhì)追索和勞動追索。同時,對公有制邏輯的梳理,既要著眼于“抽象歷史行動”(所謂的私有制的發(fā)展與自我揚棄),也要著眼于“具體歷史行動”,考究歷史上公有制建設(shè)因素的培育。然則,《資本論》仍舊沒有滿足于對“現(xiàn)實的歷史”的刻畫,而是提升該種刻畫的規(guī)定,使之立足了“現(xiàn)實的歷史”批判(參看《保衛(wèi)》第一章)。從批判出發(fā),根本拒絕了知識演繹,摒除了邏輯起點假設(shè)妄想。既研究“客體批判”,也研究“主體批判”,就迫使我們系統(tǒng)研究人類發(fā)展意蘊的“全史”和機制構(gòu)造作用的“整史”。這是“實踐化的”(行動的和活歷史的)批判規(guī)定:既窮究物質(zhì)發(fā)展的全部可能性,也窮究人的全面發(fā)展,而滿足了對于發(fā)展類型(或曰“歷史前進道路”)的全面追索性。經(jīng)濟形態(tài)社會構(gòu)造總示意如圖1所示。

圖1 經(jīng)濟形態(tài)社會的基本構(gòu)造
上圖表明了生產(chǎn)單位和消費單位的“總體關(guān)系”。它主要告訴我們,《資本論》完結(jié)的是商品經(jīng)濟形態(tài)的大寫字母的社會發(fā)展邏輯,扼要說明的是“商品-資本批判”(以勞動二重性為歷史支架和認識支架)。【注:相關(guān)論述參閱《保衛(wèi)》首版后,筆者發(fā)表的文章:《的藝術(shù)高度:社會客觀批判——關(guān)于“商品批判”和“資本批判”的歷史辯證法》(《上海對外經(jīng)貿(mào)大學(xué)學(xué)報》2016年第1期)】

要之,全部的批判邏輯包括了主體批判和客體批判兩方面的客觀內(nèi)容。而對前者的把握最終需要落實到“以人為本”行動方略上來。這項工作唯其“深刻”,在于從歷史發(fā)展全局查明了“物質(zhì)生產(chǎn)和它所包含的關(guān)系”:主體人的發(fā)展的活動二重性,又毋寧說,它在商品經(jīng)濟形態(tài)系統(tǒng)中就表現(xiàn)為“勞動的二重性”。據(jù)此指明:資產(chǎn)階級社會由于迫使勞動的這兩方面性質(zhì)(有用勞動和人類勞動)的對立的深化,而加劇了主體自身體系的分裂,促成勞動的二重社會發(fā)展,遭致“經(jīng)濟矛盾”日益嚴重之歷史后果。

這里需要額外說說《資本論》條目體與貫通法。《<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序言》言明馬克思當時以“條目體”——所謂的《六分冊計劃》,總攬“商品-資本”之研究。后改以《資本論》四卷結(jié)構(gòu)體式,這樣說來,《資本論》乃是一巨型的“資本條目”,而又以同樣巨型的“商品條目”為基礎(chǔ),實現(xiàn)了邏輯批判意義的“史通”。蓋言“資本論”,以商品批判資本也,復(fù)求商品批判之歷史規(guī)定,于是得到關(guān)于“商品-資本批判”之全體理論。【注: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在工作內(nèi)容上可確定為“實踐地批判”、“總體地批判”、“內(nèi)在地(理論)批判”以及“全面地(認識)批判”,而統(tǒng)領(lǐng)以“歷史地批判”和“辯證地批判”(參閱拙文《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的多重規(guī)定與研究意蘊——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當代經(jīng)濟研究》2018年第7期)】
概言之,歷史研究注重貫通之法。貫通是“縱通”、“橫通”的總和說法。所謂:“今之專史、斷代史都可屬于橫通”,“橫通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立價值,前提是不作井底之蛙”,概言之,“通史的‘通’為綜合性的‘縱’通”,“縱通也必須建筑在橫通的基礎(chǔ)上,其養(yǎng)料必然來源于橫通的供給,活水源源不絕,再加巧妙經(jīng)緯,方不至于膚淺漂浮而不落實地。” 【注:王家范. 中國歷史通論.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緒言. 2000:10.】

由此,需要從學(xué)科建設(shè)和工作邏輯的層面處理好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諸范疇的辯證界劃關(guān)系,由于確定了界限,“它不抹殺現(xiàn)實差別”;手段是“構(gòu)圖”,但在這些過程中,既要防止邏輯主義的作風,又要避免陷入“知識論的解釋學(xué)”窠臼。例如說,唯物史觀判定“權(quán)力”的依據(jù)是由上層建筑而及于生產(chǎn)關(guān)系,由生產(chǎn)關(guān)系而及于生產(chǎn)力。但不能以“此權(quán)力”任意解釋“彼權(quán)力”。在如何研究“權(quán)力”的問題上,現(xiàn)有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似乎陷入了理論窘境:既然生產(chǎn)力作為“第一權(quán)力體系”,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何不優(yōu)先研究它?其實,這是“客體批判”學(xué)科定位和內(nèi)部研究權(quán)屬的分配問題。概言之,是要認識到:“人類史前時期的社會科學(xué)研究服從于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工作邏輯,以‘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客體批判’為工作領(lǐng)銜。這就是勞動二重性的基本工作原理:主體和客體構(gòu)成了歷史運動辯證法的主角,但客體批判的力量始終高于主體力量。這種史實摧垮了‘生產(chǎn)力純經(jīng)濟學(xué)’認識神話,但恰當?shù)靥岢隽丝茖W(xué)界定‘客體批判’研究性質(zhì)的問題。”【注:深入的分析、邏輯的考量和方法論層面的討論,詳見拙作:《生產(chǎn)力研究維度和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xué)的創(chuàng)新——兼析“客體批判”的研究性質(zhì)》(《當代經(jīng)濟研究》2017年第2期)】
產(chǎn)品和商品規(guī)定性的不同是區(qū)分兩種經(jīng)濟形態(tài)的特質(zhì)性規(guī)定。由此,我們需要分析產(chǎn)品和商品的社會構(gòu)造規(guī)范。從批判規(guī)定的角度看,產(chǎn)品的構(gòu)造成分是“物質(zhì)”(物質(zhì)產(chǎn)品)和“身份”(社會產(chǎn)品),商品的構(gòu)造成分是“物質(zhì)”(使用價值)和“財產(chǎn)”(價值);與前者對應(yīng)的顯然是“身份統(tǒng)治”歷史世界,與后者對應(yīng)的顯然是“財產(chǎn)統(tǒng)治”歷史世界。統(tǒng)一二者的則是“生產(chǎn)物”,或曰“社會生成物”(規(guī)定)。例如說,“商品是由生產(chǎn)物發(fā)展過來的。不論怎樣一件簡單的生產(chǎn)物,如一探究它發(fā)展成為商品的全過程,或者,如從一個簡單的商品交換現(xiàn)象中,去探究隱藏在它背后的本質(zhì),就知道商品是把一定的社會關(guān)系,作為它形成的現(xiàn)實基礎(chǔ)。它體現(xiàn)著現(xiàn)實的社會關(guān)系;同時,還可由它形成的過程,測定一個社會的生產(chǎn)力的發(fā)達水準。”【注:王亞南. 中國經(jīng)濟原論.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12:72.】因此,產(chǎn)品和商品毋寧被稱作“生成規(guī)定”,它們的區(qū)別僅僅是生成狀況不同,兩者的對立集中于“身份關(guān)系”(社會產(chǎn)品本身)和“財產(chǎn)關(guān)系”(社會總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規(guī)定)的社會關(guān)系的分野。
二重性貫通之“歷史”和“方法”乃在于形成主體、客體共演的社會歷史結(jié)構(gòu)。身份本位和勞動本體,這是主體側(cè)與客體側(cè)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相得益彰的規(guī)定所在,然而,必須從批判的進路上將兩者真正結(jié)合起來。據(jù)之,我們談?wù)撝黧w人的物質(zhì)身份活動(或者說物質(zhì)身份活動向度的勞動)對于“物質(zhì)”的創(chuàng)造性、主體人的社會身份活動(或者說社會身份活動向度的勞動)對于“身份產(chǎn)品”的創(chuàng)造性,以及主體人的有用物質(zhì)勞動對于“使用價值”的創(chuàng)造性和人類抽象勞動對于“價值”的創(chuàng)造性,此四維的創(chuàng)造活動必然歷史地結(jié)合起來考察,又必須現(xiàn)實地結(jié)合,以發(fā)掘勞動和物質(zhì)自由結(jié)合之歷史成長力量。歸根結(jié)底,馬克思說的“體現(xiàn)于……勞動的二重性”句式所指示的發(fā)展向度的意義,應(yīng)該就是“人的活動的二重性”的歷史轉(zhuǎn)化表現(xiàn),從而,需要越出純工藝學(xué)的范疇重新考察人類學(xué)基礎(chǔ),尋找更廣泛的人的合類性規(guī)定。要之,必須認識到,產(chǎn)品的“兩因素”同樣是類規(guī)定的存在者,其類的性質(zhì)和類的量,實際反映的就是身份勞動的特殊質(zhì)和量。物質(zhì)身份勞動產(chǎn)生特殊物的規(guī)定,與之契合的各種社會身份類型主體的勞動(即“社會身份勞動”)生出產(chǎn)品的“社會身份”規(guī)定,使產(chǎn)品成為“社會產(chǎn)品”。產(chǎn)品和商品和而不同。我們在強調(diào)“產(chǎn)品變商品”的同時,必須加強對產(chǎn)品社會經(jīng)濟功能的基礎(chǔ)作用及制度基礎(chǔ)設(shè)施的研究。同時,必須認識到,無論“身份二重性”(主體人勞作時的物質(zhì)身份和社會身份)抑或“勞動二重性”(主體人作為“物質(zhì)勞動”和“社會財產(chǎn)的勞動”的二重規(guī)定),其源頭和發(fā)展的向度均是“人的活動二重性”;它們互為工作規(guī)定的對立面,由此完結(jié)了行動主體的不同經(jīng)濟性質(zhì)。
進一步,主體人的活動二重性——物質(zhì)主體(行動)和社會主體(行動)——是直截了當?shù)?ldquo;行動二重性”(把主體視為“行動”規(guī)定)。勞動者的身份行動規(guī)定則構(gòu)成對資產(chǎn)階級物象二重性的“正面理論出擊”。它所對應(yīng)的主體概念是“族民”及其衍生的組織化、社會化的主體關(guān)系。從而產(chǎn)品,既是物質(zhì)產(chǎn)品,是物質(zhì)產(chǎn)品在人類學(xué)意義上的直接的發(fā)展,也是主體的個性化身份關(guān)系的發(fā)展載體,是“身份產(chǎn)品”,是社會合類的勞動人學(xué)基礎(chǔ)。【注:這樣才能說明從物質(zhì)生產(chǎn)方式中升騰出來的“中華社會生產(chǎn)方式”,所謂“無為而為”(道生之、“無”生化“有”的發(fā)生學(xué)或者說行動邏輯),所謂“陰陽”、所謂“體用”(母子工作思維和語言),所謂“泱泱大國”、所謂“大一統(tǒng)”(家國占有關(guān)系的主導(dǎo)性),所謂“中庸之道”(居中而用,即,中者尋求標準也,庸者善用也),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主體行動路線和方略),都因應(yīng)了上述生產(chǎn)方式的概念,從而醞釀了生生不息發(fā)展的中華所有制及其衍生的主體間的合作交往關(guān)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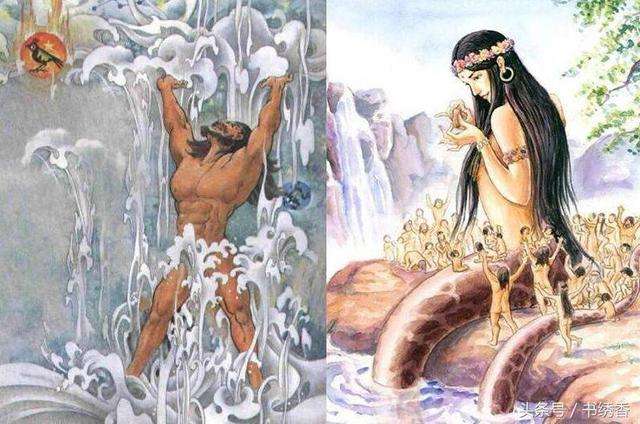
這樣的架構(gòu)在支持“商品批判——資本批判”之揚棄工作同時,著力培育“產(chǎn)品批判——社會主體批判(勞動批判)”之工作路徑,從中升華出真正意義的現(xiàn)代主體活動規(guī)定。這表明,即便著眼于客體批判,也可從中求索出《資本論》“體”“學(xué)”“用”一體化的方法論問題。通的結(jié)果是肯定《資本論》是史書,并且是“通史體裁”史書。這啟發(fā)我們:既要建立王亞南模本的“中華《資本論》”研究,同時,也要適時創(chuàng)設(shè)和推廣“中國批判”范疇。就根本而言,前者的實質(zhì)性工作還是推廣“中國化”,使“馬克思原創(chuàng)”成為中國方法,后者的工作著力點則是深度挖掘“中國原創(chuàng)”。據(jù)此,勞動一般的“行動”在先,是一個從“無”到“有”的歷史過程。而產(chǎn)品經(jīng)濟形態(tài)恰好對應(yīng)此“無”(生成狀態(tài))的歷史過程,它和“有”之經(jīng)濟規(guī)定具有社會空間的并存性。這就豐富了“勞動一般”:方便我們直接從分配關(guān)系入手,來說明“社會勞動”之發(fā)展。

三、中國主體批判的深層歷史構(gòu)境
在物的發(fā)展體系下,人的勞動發(fā)展為“物關(guān)系”所掩蓋和役使,從而,社會發(fā)展具有“物役性”。物役性導(dǎo)致《資本論》中的“人類行動主體”似乎被理論刪除了(例如阿爾都塞從中讀出了“無主體的結(jié)構(gòu)”),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社會”為工作跳板區(qū)分出主體類型的三種歷史發(fā)展形式:“第一形式”是強制合作型交往關(guān)系,“第二形式”是獨立個人關(guān)系的非合作型交往,“第三形式”是條件必然性得到根本解決的社會共同體自由個性類型的交往關(guān)系。交往是主體的直接訴求,誘導(dǎo)哈貝馬斯做出如此判斷:“馬克思并不是按照一個社會的復(fù)合性的增加來評價這個社會的發(fā)展,而是根據(jù)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水平和社會交往形成的成熟與否來評價社會發(fā)展。”【注:哈貝馬斯. 郭官義譯. 重建歷史唯物主義. 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 2000:152.】但是,這種主體實踐是從資本的歷史向度做出的,和個人所有制的前兩個發(fā)展階段(以自己勞動為基礎(chǔ)的單純個人所有制和以雇傭勞動為基礎(chǔ)的資本家所有制)相呼應(yīng)。例如,對應(yīng)“第二形式”的是商品經(jīng)濟形態(tài)社會中“異己的、對抗的主體”概念。
三種歷史形式對主體發(fā)展的規(guī)定是單維度的,馬克思肯定它的存在性,但同時強調(diào)了兩個兼容性基礎(chǔ):人的依賴關(guān)系和物的依賴性。“物的依賴性”是針對客體維度,“人的依賴關(guān)系”則僅針對主體發(fā)展本身(所謂的“賦予人以支配人的這種權(quán)力”)。所以,需要把第一形式的“延伸或發(fā)展形態(tài)”考慮進來。人的全面發(fā)展建基于上述兩大基礎(chǔ)的發(fā)展:“主體的依賴關(guān)系”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內(nèi)涵的發(fā)展和“客體的依賴性”的歷史揚棄意義的發(fā)展。這樣看來,所謂“第二個階段”(第二大形態(tài)或第二形式),也是不獨立的,寧可說成和第一形式的發(fā)展形態(tài)歷史同步,又和“新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萌芽因素”發(fā)展同步。前者如恩格斯的確認:“隨著家長制家庭的出現(xiàn),我們便進入成文史的領(lǐng)域”,但是,“對這一點,馬克思補充說:‘現(xiàn)代家庭在萌芽時,不僅包含著奴隸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著農(nóng)奴制,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勞役有關(guān)的。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來在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發(fā)展起來的對立。’”【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70.】
后者如《資本論》所確證的“工人合作制”的現(xiàn)代萌芽發(fā)展。要之,一旦把主體具體類型和客體財產(chǎn)類型基于歷史時空條件結(jié)合起來考慮,所有制關(guān)系的內(nèi)涵即得以飽滿化。此為統(tǒng)一構(gòu)造“生產(chǎn)關(guān)系-交往關(guān)系”意義之可能。深一步而言,其實,這里同樣還存在著第一形式和第三形式“直接耦合”的情形:如在中國社會,它表現(xiàn)為“家——國”和“國——家”運動鏈條的成長。【注:延展性的探討,參閱拙作:《在何種意蘊上是“史書”——兼析<21世紀資本論>的歷史書性質(zhì)》(《江漢論壇》2016年第5期)】
同樣,中國文明的早熟性及其近代的衰落,亦只能由此來說明。于是乎,可以闡明中國國有企業(yè)發(fā)展的歷史特性:肇始于“家國社會”,成型于“國領(lǐng)導(dǎo)家的中華帝制時代”,而最終作為“社會主義工廠”發(fā)展成長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現(xiàn)當代。【注:拙作《中國國有企業(yè)歷史特性分析》(《經(jīng)濟評論》2008年第1期)提出中國歷史上的國有企業(yè)是二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和官民經(jīng)濟統(tǒng)合斗爭的產(chǎn)物,是特殊的科層生產(chǎn)方式與企業(yè)經(jīng)濟形式。實際上,它是一部生產(chǎn)勞動組織的“通史”,蓋言“純粹官營工場”、“官營工場+分包制”、“官營工場或工廠+準工業(yè)化”、“國家工廠+計劃科層制+工業(yè)化”、“現(xiàn)代企業(yè)組織+現(xiàn)代分包制度+市場化”的發(fā)展類型的特質(zhì)繼承、組織結(jié)構(gòu)累積與經(jīng)濟形式流變,實際所整合者即“主體”和“客體”兩個維度的發(fā)展內(nèi)容。如中國勞役制向雇工制的歷史轉(zhuǎn)化,如因應(yīng)生產(chǎn)規(guī)模和商品經(jīng)濟市場擴大需要的組織科層管理的創(chuàng)設(shè),再如和租稅制度結(jié)合的社會再生產(chǎn)的調(diào)適與控制等等,無不顯示出中華身份合約與特殊財產(chǎn)合約的內(nèi)在契合性。從而切合了中國固有的所有制關(guān)系,在內(nèi)涵邏輯上體現(xiàn)為“家”、“科層”、“企業(yè)”“國”四位一體的運行樣態(tài)。可見,單單是“產(chǎn)權(quán)契約”無論如何容納不了它的歷史軌跡(貫通宗法關(guān)系、經(jīng)濟關(guān)系和國家關(guān)系)與獨特社會經(jīng)濟作用(大一統(tǒng)制度架構(gòu)下的政治經(jīng)濟功能)。】
導(dǎo)致有史學(xué)家驚呼:“總之,在傳統(tǒng)中國,私有制的發(fā)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發(fā)育的法制保障。如此,中國進入現(xiàn)代的艱難才可以被理解。”【注:王家范. 中國歷史通論.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0:10.】
要之,劃分歷史經(jīng)濟形態(tài)的依據(jù)不獨為客體標準,主體發(fā)展規(guī)定亦是一考慮項。例如,中國社會向來貫通于“家事國是”乃至“家國天下史”,所以有此生長規(guī)定:道恒無名,樸雖小,而天下莫能臣也!并且蓋因“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于江海”,而能達到主客體互系境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則,吾何以知天下然哉?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xiāng)觀鄉(xiāng),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此種境界若單獨從主體方面來講,則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則不相往來。【注:根據(jù)此處論述,小國寡民乃行“民至之治”,家或鄉(xiāng)也,此和而不同之家國社會也。中國人強調(diào)身份主體及其治理“各各不同”,然而彼此循序漸進、親和而貫通。故《管子·牧民》有此詳盡言論:以家為鄉(xiāng),鄉(xiāng)不可為也;以鄉(xiāng)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xiāng)為鄉(xiāng),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xiāng),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jié)!】
可據(jù)此得出這樣的觀點:“從發(fā)生學(xué)過程來看,中國傳統(tǒng)社會歷史是沿著一條自然演變的路線前進,個人的‘主體性’從來沒有獨立過。”【注:王家范. 中國歷史通論.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0:127.】
即是說,中國沒有典型態(tài)的獨立個人財產(chǎn)意義的私有制的歷史發(fā)展。“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由于缺乏健全發(fā)育和法制保障的社會環(huán)境,私有產(chǎn)權(quán)的發(fā)展是不充分、不獨立、不完全的”,于是可以說,“‘公私’就這樣混成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注:王家范. 中國歷史通論.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0:139.】但同時,又不能說中國歷史上不具有財產(chǎn)制度,董仲舒說:“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從中顯見了財產(chǎn)觀念在古代中國社會當中的普及性。嚴格意義說,中國只是不具備私人財產(chǎn)極致發(fā)展的歷史土壤,而極力地把“財產(chǎn)”融入身份管理制度和體系中罷了。【注:如王安石的言論及評價:“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于后世之紛紛乎?”“他看得天下之物,是天下人所公有;當由一個代表正義的人,為之公平分配,而不當由自私自利的人,擅其利而私其取予,以役使眾人;其意昭然若揭。”(呂思勉. 呂著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 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2013:112)】
剪不斷,理還亂。不同占有主體類型是如何貫通的,以及相應(yīng)地,公有制的占有主體是如何具體地歷史發(fā)生的,是需要通盤考慮的一事體。為全面理解問題,需要同時考究家有制、國有制的縱通與橫通,便于形成對“貫通性”的內(nèi)在性把握。從經(jīng)濟層面看,中國家國形態(tài)當以“地租攫取型社會”表征之,這樣可把組織學(xué)的通常意義的科層建設(shè)和宗法制、官僚制統(tǒng)合起來。【注:從中提示一點,“我們不能簡單地像西方學(xué)術(shù)那樣只用‘科層制化’(bureaucratization)或(科層制化了的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等概念去理解中國現(xiàn)、當代的地方治理。”(黃宗智. 經(jīng)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jīng)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前言. 2007:8)】
中國式的國家則以“賦稅管理型國家”續(xù)代之。【注:這里我們把“中國勞役”(剩余勞動范疇意義的),同樣視為賦稅的范疇,從歷史實踐看,勞役包括在廣義的賦稅之內(nèi)。賦稅和徭役(勞役)在中國合稱“賦役”。勞役稅制是中國最古老的賦稅制度。隨著時代推移,實物和貨幣賦稅漸漸占主流,勞役稅退居次要位置。但如上文指示,勞役制在中國始終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始終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從“縱通”看,家有制具有家私有制和家公有制兩種發(fā)展樣態(tài)或類型,同樣,國有制亦可有兩種:國私有制和國公有制。但是,構(gòu)成產(chǎn)品經(jīng)濟形態(tài)占有主體內(nèi)部過渡規(guī)定的是“家私有制向國公有制的歷史過渡”,這就把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橫通性”(特別是打破了家私有制和家公有制之間的“非此即彼”的關(guān)系)歷史發(fā)展化了;或者毋寧說,內(nèi)部過渡以“家私有制向家公有制的歷史過渡”規(guī)定為發(fā)展上的小循環(huán),而以“家私有制向國公有制歷史過渡”的本身為發(fā)展上的大循環(huán)。大循環(huán)中圈套了無數(shù)的發(fā)展意義的“歷史小循環(huán)”,這樣才提供了國私有制和國公有制“社會橫通”的理論上的可能。
地租顯然是經(jīng)濟層面家有制之實際發(fā)起者。在中國,地租的“共主”是廣泛意義的。這就是“家(單位)”的深厚性。例如說,“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人際關(guān)系主要有三種連結(jié)方式:血緣、地緣和業(yè)緣(業(yè)緣當作泛義解,包括政治的、經(jīng)濟的‘同業(yè)’關(guān)系)。細致考察,不難發(fā)現(xiàn)歷史上的社會互動模式雖時有程度不同的變遷和演進(從上古的宗親合一、封邦建國,到中古的門第郡望、門生故吏,到近世的同鄉(xiāng)會、商幫、會館公所),但以家長制為核心的血緣在中國社會中始終是最具原生性的人際互動模板,屬于社會深層結(jié)構(gòu)性質(zhì)的東西。地緣和業(yè)緣無不受到血緣傳統(tǒng)力量的浸染融解,往往畸變?yōu)閹в衼喲壔驕恃壣实幕旌闲蜆邮剑c西方有別。”【注:王家范. 中國歷史通論.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0:10-11.】

“家社會”是地租關(guān)系【注:這是除開必要產(chǎn)品,而共享“剩余產(chǎn)品”的經(jīng)濟關(guān)系。】之高度性的普遍發(fā)展,是為“地租攫取型社會”。它是排賦稅的。【注:例如,東晉偉大詩人陶淵明提出過“不納賦稅”的設(shè)想。設(shè)想體現(xiàn)在對“國家公地社會制度”的理想設(shè)計的寄托中。具體的倡議是:社員租種國家公地,地租直接交給國家,余者自給自足,國家以租收解決社會公益支出,這樣,國家僅僅是“租收管理單位”,是家單位的直接延續(xù)或代理。】
這是“家”和“國”的外在對抗性。實際上,歷史上的國家正是從對“家單位的租”的奪取關(guān)系中產(chǎn)生的,從中可察見最初含義的“國家”是軍事制國家。“軍事國家”是最初時期的私有制發(fā)展的最高形態(tài),也是極端形式。【注:所謂“納貢社會”的概念,亦是“軍事國家”存在性的一個歷史佐證。因為它言明:只要絕對地存在程度不同的種種人身的依附關(guān)系,“勞動者都需要向非勞動者納貢”,這是一種“勞動保護的稀缺性”。(李建德. 經(jīng)濟制度演進大綱. 北京:中國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 2000:123)中國與之匹配的一個概念則是“王有制”。所謂:“這種‘王有制’的產(chǎn)權(quán)擴展主要建立在軍事統(tǒng)治的基礎(chǔ)之上,本質(zhì)上是軍事征服、軍事殖民的產(chǎn)物。‘產(chǎn)權(quán)’的提升主要不是通過對土地實施重新界定(分配)來實現(xiàn)的,而是憑借‘權(quán)力’為后盾,通過征調(diào)實物和人力的形態(tài),間接體現(xiàn)其為‘天下’的‘共主’地位。”(王家范. 中國歷史通論.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0:108)】
它以“極端的家形式”壓制了個人財產(chǎn)關(guān)系的成長。歷史解決的辦法是找到了“宗教國家”這一有效的替代形式。宗教制國家可以看作是對軍事制國家的外在的揚棄:“各部落之間的聯(lián)盟是相當松散的,相互爭斗時有發(fā)生,為了爭霸,那些有作為的領(lǐng)主率先在本部落實行變革:一是削弱內(nèi)部貴族勢力,強化集權(quán);二是鼓勵、支持商業(yè),實行重商主義,增加財政和軍事力量。這樣,導(dǎo)致城市和市民社會的形成。”【注:劉永佶. 勞動主義. 北京:中國經(jīng)濟出版社. 2011:457.】
與之相反,中國是沒有宗教的;中國的家是具體的,沒有抽象的“家”“國”概念。而實際上,秦滅六國倚靠的是軍事手段和“政治國家”的制度實體這兩項法寶。秦以郡縣制首開“中國官僚政治”,喚醒了“家國意識”。史考這種政治意志又是由商鞅變法予以鞏固的。“《商君書·墾令》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歷史文獻。這是商鞅為秦國起草的關(guān)于耕墾荒地的一道法令,共提出了20項對策,涉及地稅制度、商品稅制度、徭役制度、刑罰制度以及取消貴族特權(quán)、防止貪污、壓抑商人、制裁奢逸等政策,有似綱領(lǐng)性文件。其宗旨都服從同一個主題:督促民眾積極耕墾土地,實現(xiàn)以耕戰(zhàn)強國的目標……這里出現(xiàn)的‘公作’與‘私作’兩個概念非常重要——受田農(nóng)民耕墾私田外,必須為國家負擔‘公作’。‘公事’、‘私事’是密切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的,兩者不可或缺……因此,從整體上看,授田是手段、前提,賦役是目的、效果,相因相成,是一項不可分割的國家主義性質(zhì)的體制。”【注:王家范. 中國歷史通論.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0:129.】
于是,歷史上出現(xiàn)了兩種式樣的國家演進序列:“軍事國家-宗教國家”和與之對峙的“軍事國家-政治國家”。中華社會屬于后一發(fā)展類型。政治國家之建制實際上建立了“賦稅分割地租”的穩(wěn)定性制度安排。【注:王亞南將支持中國官僚政治高度發(fā)展的建設(shè)性因素歸結(jié)為兩大歷史杠桿:兩稅制和科舉制。特別是兩稅制,幾乎可以說成是中國官僚社會的經(jīng)濟制度本質(zhì)。“均田制度及其伴行的租稅制的失敗,不僅說明流通經(jīng)濟相當發(fā)達的官僚社會,不可能再把土地與農(nóng)民束縛定著起來,不使變賣,不使移轉(zhuǎn);并還說明這種社會由長期因緣積累起來形成的門閥及其有關(guān)的社會政治勢力,再不會允許把他們已經(jīng)領(lǐng)有或?qū)⒁〉玫耐恋厮袡?quán)權(quán)力,交由中央政府統(tǒng)制支配……所以,把極有彈性的租稅體制作為一個調(diào)節(jié)的杠桿:在原則上不讓步,有土斯有稅,有人斯有役;而在實施上不堅持,擇其可稅者而稅之,就其可役者而役之。那就成了恰當好處和面面兼到的靈活妙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社. 1981:81-84)】
這是“以消費為中介”的生產(chǎn)類型的發(fā)端,而全面啟動了社會產(chǎn)品配置的再生產(chǎn)行動。其突出地表現(xiàn)為賦稅管理,又完全建基于“家社會”,——這就是中華樣態(tài)的國家管理的“數(shù)目字的算計”。有史家稱:“很明白的事實,古代中國為什么要由租庸調(diào)制演變到兩稅制,再到一條鞭,最后到地丁制?不就是國家(王朝政府)意識到社會實際情形變化了,要保證一定的‘數(shù)目字’到手,賦稅管理規(guī)則不得不隨時而靈活變化……更不用說在‘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這數(shù)目字管理的嚴密!”【注:王家范. 中國歷史通論.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0:5.】
思想認識上的反映則是“家國天下觀”和“民為邦本、民富國實”的國家政治經(jīng)濟觀;“賦稅管理型國家”并且導(dǎo)致中華“經(jīng)濟的理論分析也大都由主管財政經(jīng)濟的官員做出”,因而“是典型的財政與經(jīng)濟相結(jié)合的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注:林光彬:《我國是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的創(chuàng)始國》,《政治經(jīng)濟學(xué)評論》2015年第5期】而黃仁宇則以明朝的財政管理為例,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問題的實質(zhì)與復(fù)雜性:“明朝力圖在一個廣大的帝國內(nèi)強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權(quán)的財政制度,這種做法超出達到這種程度的技術(shù)水平。”于是,他感嘆到:“明帝國缺乏與其他國家和民族進行軍事和經(jīng)濟競爭的意識,因此,并不關(guān)心行政管理效率,即使政治制度惡化,也不會立即導(dǎo)致危機,人民對行政管理不善有著相當大的忍耐力。”【注:黃仁宇. 阿風等譯.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01:408-416.】這顯然是一個反面的歷史實例,但說明了“中國財政稅收”的非獨立的性質(zhì)。

由此,也印證了把傳統(tǒng)家有制和國有制歸并為“統(tǒng)一化地租社會”予以考慮,目的即在于把握地租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類型。蓋因地租社會形態(tài)統(tǒng)一了上述“地租攫取型社會”和“賦稅管理型國家”。如《保衛(wèi)》第四章列舉馬克思的說法:“在重農(nóng)學(xué)派看來,剩余價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從簡潔處起論,地租與剩余價值構(gòu)成理解產(chǎn)品社會和商品社會經(jīng)濟關(guān)系之“樞紐”。這樣可以類推:地租社會的發(fā)展同樣是由“絕對的地租攫取”擴展為“相對的地租攫取”,靠的是國家賦稅管理杠桿【注:黃宗羲定律,是這一杠桿作用之負面效應(yīng)的說法。】,以致有黃宗智所謂“內(nèi)卷化”和“過密型經(jīng)濟增長”界說。在地租經(jīng)濟社會中,地租攫取往往依靠行政力量作保證,從而,絕對產(chǎn)品地租之攫取就是制度的平均值。而所謂相對產(chǎn)品地租之攫取則取決于賦稅管理水準和制度設(shè)計藝術(shù)。這樣,我們可簡單對應(yīng)“地租攫取型社會”(基石是家有生產(chǎn)制度)與“剩余價值攫取型社會”(基石是工廠制度)以及“賦稅管理型國家”(王朝)與“國民收入管理型社會”(現(xiàn)代國家),得出結(jié)論:一者是多元主體協(xié)作的“共主”統(tǒng)治關(guān)系,一者是“二元對立”的統(tǒng)治關(guān)系;一者遵循“等級身份”分配規(guī)律,一者遵循“平均利潤”分配規(guī)律。即如果說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相對的地租”(級差地租)之獲取是社會發(fā)展必然,從而資本家階級養(yǎng)活“地主”(土地所有者)的方式就是創(chuàng)制“級差地租——絕對地租”經(jīng)濟成長方式,那么,“等級身份”之賦稅管理是導(dǎo)致“相對的地租”(具有生產(chǎn)發(fā)展水準的產(chǎn)品地租供給)的攫取乃是社會偶然的,由此,轉(zhuǎn)而更加依賴了對“絕對的地租”的攫取。這是招致帝制大一統(tǒng)時代制度內(nèi)斂型特征取向的內(nèi)在根由。
產(chǎn)品經(jīng)濟形態(tài)向內(nèi)之內(nèi)斂型發(fā)展和商品經(jīng)濟形態(tài)向外之擴張型發(fā)展由此分野,分別定位不同的剩余產(chǎn)品生產(chǎn)模式。基于歐洲剩余價值生產(chǎn)的充分的擴張性,使得馬克思有理由相信后者能夠“吞噬”前者。由此,他強調(diào),“現(xiàn)代形式的地產(chǎn)是資本對封建地產(chǎn)和其他地產(chǎn)發(fā)生影響的產(chǎn)物”,而“現(xiàn)代地產(chǎn)的最后產(chǎn)物就是雇傭勞動的普遍確立”;馬克思以試圖有別于傳統(tǒng)地產(chǎn)經(jīng)濟規(guī)定之“現(xiàn)代地產(chǎn)”為中介作用規(guī)定,闡述“雇傭勞動”的歷史產(chǎn)生,目的在于說明經(jīng)濟形態(tài)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上的依存性。在此基礎(chǔ)上,又必然產(chǎn)生“樞紐范疇”的歷史性變革:“地租”一躍而變身為“剩余價值”,是社會主體結(jié)構(gòu)大變局的結(jié)果。這就是“身份生產(chǎn)關(guān)系”統(tǒng)治形制之于“財產(chǎn)生產(chǎn)關(guān)系”統(tǒng)治形制的歷史轉(zhuǎn)換性。無疑,歐洲社會統(tǒng)治形態(tài)的轉(zhuǎn)換是歷史徹底的,所謂的“走出中世紀”。“青年馬克思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前市民社會中的‘政治’階層在市民社會中已經(jīng)變成了純粹的‘社會’階層;但是,賦予它們作為社會和國家的中介的政治功能,無法與‘在政治領(lǐng)域自身當中把人們趕回到其有限的私人領(lǐng)域的嘗試相提并論’。”【注:曹衛(wèi)東譯. 哈貝馬斯精粹. 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 2004:101.】
馬克思的另外的一個考慮因素則是:土地所有制(地產(chǎn))的“崩潰”應(yīng)當是系統(tǒng)的,從而在“現(xiàn)代地產(chǎn)”和“傳統(tǒng)地產(chǎn)”之間具有必然的內(nèi)在承繼,而這一“承繼”恰好就構(gòu)成資本與雇傭勞動之“中介”,因為,這是“歷史的過渡”。當然,馬克思當時還無法考察中華所有制結(jié)構(gòu)中“地產(chǎn)”的多重占有身份之“非解體”性質(zhì)。例如,以皇權(quán)為代表的國家地產(chǎn)和地主土地所有制基于身份上的不可分性及其與家產(chǎn)制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使得“身份與財產(chǎn)合一型”的地租攝取體制必然嚴重依靠“管理型國家”的存在,并不斷被賦以“合法性”地位。
政治國家是身份關(guān)系的聚合體和垂直管理機構(gòu),是“身份”和“收入”對接的制度創(chuàng)設(shè)。“‘大一統(tǒng)’與‘封建制’最鮮明的區(qū)別,就在于以流動的官僚制代替世襲的貴族制,封國盡變?yōu)橛芍醒肴蚊目たh職官來治理。從此,嚴格意義上的貴族在中國不復(fù)存在。”【注:王家范. 中國歷史通論.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0:74.】
它的普及基礎(chǔ)是家有生產(chǎn)制度的發(fā)展,而形成了“基礎(chǔ)——上層”社會系統(tǒng)性構(gòu)造;就設(shè)施而論,這是家有制-國有制設(shè)施之制度主體的自下而上,謂為中國特有之制度自發(fā)秩序。【注:這里面有一個基本事實:中國“國家行政管理實際只到縣衙一級”,“中央對地方的有效監(jiān)控程度,雖有強有弱(大致與離中央的距離遠近成反比),總體水平卻遠遜于歐洲君主國。”(王家范. 中國歷史通論.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0:12)】
在“基礎(chǔ)”環(huán)節(jié)中,身份與財產(chǎn)的脫離關(guān)系一旦形成,商品生產(chǎn)和商品經(jīng)濟也就相對地發(fā)展起來。在這個時候,“賦稅管理”同樣能夠形成對價值收入和剩余價值的“強力分割”。如改革家王安石提出的“不加賦而國用足”思想,在帝國體制內(nèi)引入和刺激商品的生產(chǎn)與流通,以期達到這樣的效果:如果經(jīng)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增加。【注:王安石的想法仍然是本末學(xué)和輕重論的結(jié)合范例。這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國富論”。在重農(nóng)國策的基礎(chǔ)上,主張:“封建國家要直接進入商品流通領(lǐng)域以及部分商品的生產(chǎn)領(lǐng)域,兼用經(jīng)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經(jīng)營和控制工商業(yè),進而影響和控制整個國民經(jīng)濟,使國家在社會經(jīng)濟生活中取得舉足輕重的支配地位。”(楊松華. 大一統(tǒng)制度與中國興衰.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163)】
另外,從“稅人”到“稅地”,則意味著中國土地關(guān)系的長足的歷史發(fā)展,主體批判和客體批判的規(guī)定趨于合流。“凡此種種,都說明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自然經(jīng)濟與商品經(jīng)濟很早就平肩而行,相互交織,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程度并不很低。”【注:王家范. 中國歷史通論.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00:191-192.】
要之,勞動力商品說明的是“獨立個人之身份”,遠未窮盡身份的內(nèi)涵邏輯。關(guān)于中國商品批判以及相應(yīng)的中國資本批判的特殊發(fā)展問題,需要從對“中國身份”的多重識別的路徑考察入手。中國是關(guān)于身份構(gòu)造之極其復(fù)雜性社會。因而更進一步的做法,是需要從身份系統(tǒng)對財產(chǎn)關(guān)系制約性的分析入手,展開對“中華產(chǎn)品生產(chǎn)方式”(身份生產(chǎn)關(guān)系之生成運動規(guī)定)的歷史勘察,例如說,中國沒有典型奴隸制和封建制的“長子繼承權(quán)”財產(chǎn)發(fā)展的制度土壤,便根本束縛了資本之獨立性與社會集聚性。【注:上文指出,中國沒有典型奴隸制可從“家有制”的存在性和緣起的規(guī)定中得到說明,中國沒有典型身份統(tǒng)治關(guān)系的封建制則是由于從部落時代一步跨入“封建時代”。需要嚴格區(qū)分“封建”(封土建邦、封邦建國)、“封建制”(領(lǐng)地分封制度)和“封建主義”(即封建專制或封建主義社會之意義)。中國是“家國社會”的典型態(tài),它兼具身份和財產(chǎn)二重關(guān)系屬性,地主是憑借身份關(guān)系對土地財產(chǎn)進行的社會占有。然則,“封建主義”自然不是適合的表述,它有違于以郡縣制為治理核心內(nèi)容規(guī)定的“皇權(quán)制”政體的歷史內(nèi)涵,因此,中國“大一統(tǒng)”絕對不是從“封建”上說的,乃是專指這樣的經(jīng)濟形態(tài)制度構(gòu)造:官僚制+地主制+家產(chǎn)制度,以及它們的三位一體的社會結(jié)合性。如此也就能明白:為什么中國無法穩(wěn)定推行“長子繼承權(quán)”身份財產(chǎn)制,而要替換以“分家的財產(chǎn)制度”(土地是財產(chǎn),并非身份關(guān)系象征)。“分家制”是宗法制的身份財產(chǎn)關(guān)系規(guī)范,體現(xiàn)部落和家族內(nèi)部關(guān)系之管理方式,是“封建”的微觀運作形態(tài)。這樣說來,中國是有“封建”(即身份統(tǒng)治關(guān)系)的普遍發(fā)展而無“封建之主義”的特殊國度。領(lǐng)主封建制同財產(chǎn)資本制是有嚴格歷史繼承關(guān)系的兩種對立生產(chǎn)關(guān)系制度,這種發(fā)展情形在中國卻并不具有,要之,對中國而言,是需要從“家國社會”的特性來看待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存在性與歷史成長關(guān)系。】
中國是發(fā)展典型與制度典型的混合。中華商品生產(chǎn)方式之得不到長足發(fā)展的內(nèi)部原因在于身份制的長期歷史做大和因承沿襲。但總的來講,中華歷史之產(chǎn)品配置經(jīng)濟是內(nèi)含了“商品經(jīng)濟規(guī)定”于其內(nèi)的,主體相得益彰于客體發(fā)展。從而,主體性得到充分鞏固,主體批判得到了歷史張揚,并且建基于一定的時代物質(zhì)發(fā)展基礎(chǔ)。這些條件,使得我們這個國度能夠廣泛建設(shè)“公有制主體”,以勞動的超越發(fā)展,迎來現(xiàn)代公有制經(jīng)濟發(fā)展曙光。并且,從完成了的過渡看,中華所有制的現(xiàn)代化進程仍然直接借助了客體批判的規(guī)定:現(xiàn)實的起點是“國身份”占有主體的私有制類型向“現(xiàn)代國家所有制”之激進過渡,中間涵括“家公有制”歷史發(fā)育過程。由此,從外部表現(xiàn)出來的過渡是“商品私有制”向“產(chǎn)品公有制”的一次整體意義的“歷史大搬遷”。商品所有制類型將要逐漸被歷史革新。與此行動伴生的是產(chǎn)品所有制內(nèi)涵的“歷史更新”:單純意義的家有制和國有制的互動模式,為公有制發(fā)展與完善導(dǎo)向的“集體所有制”(所謂“集體”,即現(xiàn)代“家身份”之占有主體)和“全民所有制”(所謂“全民”,即現(xiàn)代“國身份”的特殊稱謂,是占有主體的人民化內(nèi)涵)的互動模式所更換,并內(nèi)在兼容了處于革新狀態(tài)的商品社會所有制類型。過渡是歷史的,也是現(xiàn)實的。如此,才能深刻理解諸多中間形態(tài):它們兼具“身份生產(chǎn)關(guān)系”以及“財產(chǎn)生產(chǎn)關(guān)系”特點,失掉了單純的特征,因為功能特性上的分進合擊,彼此捍格不入,它們可能使經(jīng)濟顯得不穩(wěn)定,但充滿“活力”。歸根結(jié)底,它們以復(fù)合體規(guī)定與形態(tài)賦予歷史系統(tǒng)之極大的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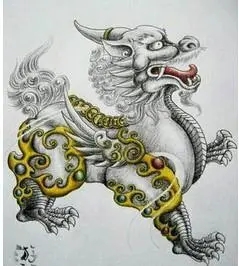
四、時代重提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的意義
時代重提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的要旨是以“批判規(guī)定”書寫中國經(jīng)濟學(xué)的脈絡(luò)、體系,確立其工作方法以及理論邏輯。這就需要主客體(批判)并舉。為此,書寫如下題旨:“畝澮敷四海,川源滌九州;既膺九命錫,乃建洪范疇。史體肥沃,并刀如水;批判志學(xué),理通實踐。”所謂鼎革鐵流,坎坎伐檀。青篙一支,曲歌淙淙。星野雄風,邏輯大用,瀟瀟起,洞庭湖面雨。滄海遺篇,史懷濃烈,文章萬種。而今歷盡滄桑,思飛遐邇,往事越千年。待從頭,笑在叢中,看山巒起伏,家國無數(shù)。總有新桃換舊符,神想無窮。心悅靈犀,彩翼雙飛,行與君同。而今識得社會主義,家國天下一張弓!【注:又之,是需要把這個地基上之建設(shè)“科學(xué)”視為史書意義的“百科全書”,遂引出“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學(xué)科性質(zhì)和統(tǒng)一歷史科學(xué)之建構(gòu)取向性。迄今為止的研究人的發(fā)展的三種方式是:效用——純粹個人的自由個性、抽象勞動——不自由的人類主體個性以及中國式的“家”和“國”——主體人的具體身份個性(介于自由和不自由之間)的成長。既成的經(jīng)濟理論體系對人的研究是從完全對立的方面進行的。這表明邁向“自由個性”的道路并不能倚靠客體批判體系的完成而一蹴而就。為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必須作為“中國政治經(jīng)濟學(xué)”之指導(dǎo)核心,而中國政治經(jīng)濟學(xué)亦必須作為“統(tǒng)一之中國經(jīng)濟學(xué)”指導(dǎo)核心的規(guī)定。據(jù)此梳理“家國社會”到社會主義之歷史成長軌跡,確立《資本論》在中國的特殊理論地位,以整體指導(dǎo)“歷史地批判”工作。鑒于此,關(guān)于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之“批判”內(nèi)涵,有學(xué)者梳理出中國相應(yīng)的說法,乃是旨在彰顯“中國行動邏輯”的一個歷史思考。這一說法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經(jīng)歷了三次重大的變革,即殷周變革、春秋戰(zhàn)國變革和唐宋變革。通過三次社會變革,中國進入三個社會發(fā)展階段,即封建社會、世族社會和齊民社會。與歷史上的社會變革相對應(yīng)的社會價值思想也經(jīng)歷了三次革命,即周文革命、儒家革命和理學(xué)革命。”(高德步. 中國價值的革命.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5)其實,基于客觀批判與主觀批判的結(jié)合以及中華道統(tǒng)的必然延續(xù),明清以降的中國革命可歸結(jié)為“學(xué)科革命”類型,這從中國地方志的學(xué)科熔爐的工作性質(zhì)上可以看出(如對“縱不斷線”、“橫不缺項”條目體的確認)。】
觀近現(xiàn)代歐洲之事,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路線的事業(yè)也,又建立在對自然科學(xué)形成“總體概念”之際。總體看,這是“知識論”盛行的時空時代。所謂知識,物之認識;廣延地看,又是事物之“自我認識”。在第五章中,《保衛(wèi)》交代了“馬克思主義之緣起”,蓋因自然科學(xué)之功。推論自然科學(xué)之成為“總體”(社會之事),又必須論及資本主義的歷史功績,此兩位一體之事功!由此呈現(xiàn)出“財產(chǎn)科學(xué)”盛事。馬克思恩格斯得以總結(jié)之,是為“所有制概念”之被提出。這個概念初以“財產(chǎn)所有制”之義行世,說明的是“商品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自我認識”。中華所不如者,蓋如是。但中華“家-國主義”之事,亦非等閑。其尤側(cè)重在“身份所有制”這一面。自然科學(xué)在中華,遠古以來一直為“私人之事”(國或家身份的私人的學(xué)術(shù)或?qū)W說傳承的事體活動),換言之,是被牢牢掌控了,此大一統(tǒng)制度之“失”。大一統(tǒng)制度之“得”(尤其是政治之得)在于一體化社會生產(chǎn)與經(jīng)濟活動,使之強力秩序化;這樣,生產(chǎn)力決非單純“客體”之概念。相比之下,馬克思《資本論》描摹的社會生產(chǎn)的發(fā)展是客體向度上的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發(fā)展的“對立統(tǒng)一”意義;所謂資本主義創(chuàng)造了“空前的生產(chǎn)力”,所謂資本主義創(chuàng)造之“社會的異化關(guān)系”,謂物質(zhì)力量發(fā)展也,謂與之對立的物化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發(fā)展也。相形之下,中華體系之“生產(chǎn)力”更加側(cè)重在“主體發(fā)展”這一面,所以,中華生產(chǎn)關(guān)系歷來是“主體型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范型。于是如果進行典型態(tài)的比較,那么相比之下,近代歐洲發(fā)起生產(chǎn)交換革命乃是“先行的”,其激發(fā)了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矛盾運動,使矛盾經(jīng)濟化、系統(tǒng)外顯化,直至社會底層化。但相形之下,中華仍局限于身份關(guān)系之重重包袱中,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嚴重受制于生產(chǎn)關(guān)系改良的狀況,本身為一高度的耦合體。此中華社會歷史之不足。中華的優(yōu)良之處則在于對“物體系”的拒絕,這樣,生產(chǎn)力有了立根之本,以人的發(fā)展為本的“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一旦獲得強大科技支撐,也就能夠煥發(fā)出極大“發(fā)展熱情”,并后來者居上。同時不容忽視的是,它對傳統(tǒng)的“沖擊力”和“瓦解力”亦是很強。
眾所周知,馬克思理論的全部意義和工作內(nèi)涵在于說清楚生產(chǎn)和交換的社會結(jié)合關(guān)系,說明規(guī)律發(fā)生作用的不同點,進一步提示出對資本生產(chǎn)予以歷史揚棄的方向來。同時,人們總彷徨于此點:產(chǎn)品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究竟是什么?如此,題寫“兩重批判”,則如心中有塊壘,不吐不快。這就有了若干成對范疇或工作術(shù)語的“新出現(xiàn)”:如主體批判-客體批判、身份(關(guān)系)-財產(chǎn)(關(guān)系)、生產(chǎn)關(guān)系-交往關(guān)系(生產(chǎn)關(guān)系-交換關(guān)系)、生產(chǎn)關(guān)系-分配關(guān)系、身份二重性-勞動二重性、事的科學(xué)-物的科學(xué)、發(fā)生學(xué)-辯證法,以及直接反映所有制歷史和社會構(gòu)造關(guān)系的“產(chǎn)品所有制-商品所有制”和“身份所有制-財產(chǎn)所有制”,等等。此等“新術(shù)語”為求中西貫通也!而《資本論》和中國典籍語義之貫通,乃是其中的紐結(jié)的關(guān)系,背后之規(guī)定又是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工作邏輯的貫通。
要之,商品社會的實體構(gòu)造是生產(chǎn)關(guān)系-交換關(guān)系,從中揭示出前后相繼的兩個發(fā)展規(guī)律,即價值規(guī)律(“市”的規(guī)律)和剩余價值規(guī)律(“廠”的規(guī)律)。自然經(jīng)濟——商品經(jīng)濟——產(chǎn)品經(jīng)濟的線性路線又作何解?面對歷史,問題并不難以解決。恩格斯怎樣強調(diào)這個問題呢?“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zhì)生活資料的生產(chǎn)和交換的規(guī)律的科學(xué)。”顯然,它的兩頭被合并,中間被分解。以至于必須堅持“產(chǎn)品經(jīng)濟形態(tài)-商品經(jīng)濟形態(tài)”并駕齊驅(qū)的歷史發(fā)展邏輯(一者解決主體批判問題,一者解決客體批判問題)。正如商品社會從來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發(fā)展道路,產(chǎn)品社會的發(fā)展也不應(yīng)當被從認識上孤立起來,同時,經(jīng)濟形態(tài)終歸還是社會形式,實體方面的規(guī)定是產(chǎn)品生產(chǎn)和商品生產(chǎn),兩者之間具有歷史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兩條道路是彼此依存共進的。產(chǎn)品社會的第一形態(tài),即它的初級態(tài),擔負為價值規(guī)律準備條件之歷史任務(wù),可視為“準價值規(guī)律”規(guī)定在起作用(社會身份產(chǎn)品對社會總產(chǎn)品的生成關(guān)系);產(chǎn)品社會的第二形態(tài),即它的高級態(tài),擔負揚棄剩余價值規(guī)律、為人類聯(lián)合體生產(chǎn)準備條件之發(fā)展任務(wù),則可看作“超剩余價值規(guī)律”取向的規(guī)定發(fā)揮作用(社會產(chǎn)品的法則重新發(fā)揮作用)。據(jù)此,可把更為一般意義的勞動發(fā)展與產(chǎn)品配置說成是準價值之運動規(guī)律,——如中國古代社會“家”的經(jīng)濟規(guī)律。產(chǎn)品規(guī)則和商品規(guī)則是歷史中形成的兩種經(jīng)濟運動表現(xiàn)。另外,也完全可以把公有制下社會生產(chǎn)的計劃和比例的組織形態(tài)意義的規(guī)律(從這一層面上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亦即“有計劃的市場經(jīng)濟”)視作超剩余價值之運動規(guī)律,——如中國現(xiàn)代社會“國”的經(jīng)濟規(guī)律。從家國社會主義到勞動社會主義的社會歷史具體實踐則表明:規(guī)律從來不是什么抽象的東西,而有著實在之經(jīng)濟內(nèi)容,是對主客體的具體發(fā)展規(guī)定的客觀陳述。【注:許光偉. 保衛(wèi)《資本論》——經(jīng)濟形態(tài)社會理論大綱. 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 2014:125.】
鑒于上述,使得我們可從歷史進程中工作取出兩個權(quán)力體系:(1)生產(chǎn)力體系——人對物的批判,以人的物化為發(fā)展指向性,或曰第一權(quán)力體系;(2)生產(chǎn)關(guān)系體系——物對人的批判,以物的人化為發(fā)展指向性,或曰第二權(quán)力體系。權(quán)力體系乃是相互嵌套的工作系統(tǒng),不是簡單并列的兩個概念層次。盡管由人來設(shè)定,第一體系說到底是發(fā)展了客體的力量,使客體成其為如下完整之存在規(guī)定:出發(fā)點是客體,通過不斷吸納主體的規(guī)定,成型為完善的客體發(fā)展體系,——在這里,被吸納的主體實際是作為“客體”看待的。馬克思在四重義項上運用生產(chǎn)力概念:一是生產(chǎn)條件,二是從生產(chǎn)條件來看的生產(chǎn)形式,三是客體,四是從客體角度對待和運用的主體概念。生產(chǎn)力發(fā)展道路是客體批判——主體批判——客體批判。第二體系因應(yīng)第一體系進行,馬克思《資本論》總以批判規(guī)定鳥瞰之,以“客體批判”特別地說明。客體批判說到底在于發(fā)展和匯聚主體的力量,使之成為“社會”:出發(fā)點是主體——主體權(quán)力的規(guī)定以及主體對客體的占有或支配,不斷內(nèi)含客體發(fā)展內(nèi)容,吸納客體規(guī)定,通過發(fā)展出客體的越來越有效服務(wù)主體的規(guī)定,使客體成為“智能自然”,而主體自身亦得以進化。以上,其實講述的是主體概念不斷完善和成型化之漸進過程。與之對應(yīng),馬克思同樣在四重義項上運用生產(chǎn)關(guān)系概念:一是生產(chǎn)形式,二是從生產(chǎn)形式來看的生產(chǎn)條件,三是主體,四是從主體角度對待和運用的客體概念。第一體系的核心工作內(nèi)容是“知識關(guān)系”(主體對物質(zhì)世界的了解)。這個過程是永無止境的開放和發(fā)展過程,直至使主體自身同樣成為物質(zhì)系統(tǒng)的智能組成——所謂人的物質(zhì)化;這就是“客體批判”的人類史前發(fā)展時期任務(wù)的終結(jié),并于規(guī)定性上向生產(chǎn)力系統(tǒng)回歸,由此開創(chuàng)人類真正形態(tài)之歷史發(fā)展時期。第二體系的核心工作內(nèi)容是“身份和財產(chǎn)關(guān)系”,即物以人格化的關(guān)系成為人的系統(tǒng)的組成。生產(chǎn)關(guān)系發(fā)展道路是主體批判——客體批判——主體批判。因此,無論生產(chǎn)力或生產(chǎn)關(guān)系,均是典型存在者的具體或抽象規(guī)定,它們均是歷史用語,而非一般科學(xué)用語。【注:許光偉:《生產(chǎn)力研究維度和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xué)的創(chuàng)新——兼析“客體批判”的研究性質(zhì)》,《當代經(jīng)濟研究》2017年第2期】
扼要地講,族民、社會勞工是由主體力量激發(fā)出來的社會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前者是“直接激發(fā)”類型,相較而言,后者是“間接激發(fā)”類型,經(jīng)歷市民——資本的迂回發(fā)展過程。市民、資本代表了純凈化的經(jīng)濟運動(馬克思集中探討的“資本”乃是純凈化的經(jīng)濟政治一體的大寫概念的發(fā)展規(guī)定),即作為系統(tǒng)客體概念(社會力量依靠客體的集成激發(fā)而出),指示商品生產(chǎn)的生發(fā)、演變及成長、演化的質(zhì)性過程。而尤其要指出,族民——社會勞工是中國主體系統(tǒng)的生成,即特殊社會形態(tài)演變和緩慢分化的過程。主體和客體在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類型上固然相異,甚至截然對立,但彼此互系而統(tǒng)一。

綜之,抽象規(guī)律僅僅存在于人們的意識中,歷史具體規(guī)律則存在于歷史具體行動中,例如,直接產(chǎn)品生產(chǎn)與個體商品生產(chǎn)之間以及組織化的社會產(chǎn)品生產(chǎn)與社會化的資本商品生產(chǎn)之間,均是相生相克狀態(tài)的具體聯(lián)系(社會空間的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關(guān)系總是“主體批判”、“客體批判”紐結(jié)關(guān)系上統(tǒng)一)。整體看,這就是人類勞動過程文明規(guī)劃的歷史態(tài)、現(xiàn)實態(tài)和未來態(tài)。
【文章載陜西《資本論》研究會會刊《<資本論>研究》(2019)第15卷P57-74】
該文轉(zhuǎn)自——保衛(wèi)《資本論》:主體批判的深層歷史構(gòu)境_中國
www.sohu.com/a/314652316_425345
2022(1)-最新閱讀——階級社會及其經(jīng)濟形態(tài)知識狀況考察
《湖北經(jīng)濟學(xué)院學(xué)報》2022年第1期(知行合一與《資本論》原理)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