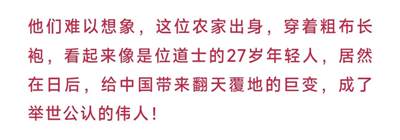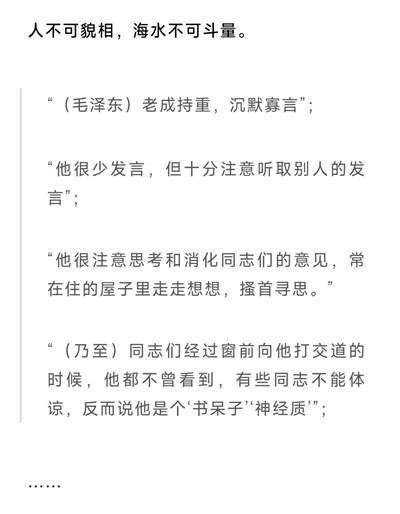1
“陳獨(dú)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guān)鍵性的這個(gè)時(shí)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dòng)上,我已成為一個(gè)馬克思主義者了。”
多年以后,在陜北窯洞,面對(duì)美國(guó)記者斯諾的提問(wèn),毛澤東這樣回憶道。
1920年夏。
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yè)2年了,和多數(shù)同學(xué)不一樣,他沒(méi)有選擇升學(xué)留洋,也沒(méi)有找份安穩(wěn)的工作做著,而是漂來(lái)漂去,漂泊不定。
此時(shí)的他,已經(jīng)從一個(gè)北漂,變成了一個(gè)滬漂。
從北走到南,單字一個(gè)“漂”。
去北京時(shí),他曾在北大做過(guò)一段時(shí)間圖書館助理員,雖被人瞧不起,但也認(rèn)識(shí)了許多牛人大咖,漲了見(jiàn)識(shí),談起了戀愛(ài),和好友遠(yuǎn)足旅行,還經(jīng)歷了五四運(yùn)動(dòng),回湖南辦了份火爆全國(guó)的《湘江評(píng)論》“現(xiàn)象級(jí)自媒體”,被軍閥“封號(hào)”后,又成功組織了驅(qū)張運(yùn)動(dòng)……
經(jīng)歷有些波折,不過(guò),總體看起來(lái)豐富多彩、成績(jī)斐然。
在李大釗先生的影響下,他的內(nèi)心,種下了馬克思主義的種子。
但,毛澤東那時(shí)的生活,似乎并未見(jiàn)什么起色,他的手頭常常拮據(jù),囊中羞澀。和現(xiàn)在去大城市打拼的沒(méi)什么背景的年輕人,頗為類似。
漂泊,似乎是那時(shí)一無(wú)所有的他,在大城市唯一的生存方式。
1920年,為了找機(jī)會(huì)同陳獨(dú)秀先生探討自己逐步確立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毛澤東決心去上海,這座被稱為“十里洋場(chǎng)”的繁華都市。
北京和上海都是大城市,如果說(shuō)在北京,還有恩師楊昌濟(jì)幫襯,那么到了上海的毛澤東,可真就是舉目無(wú)親,難上加難了。
真可謂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
更何況,為了登上開(kāi)往上海的火車,毛澤東甚至還賣掉了過(guò)冬的外衣,可見(jiàn),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對(duì)他影響之大,非常人所能為也。
在上海,他見(jiàn)到了陳獨(dú)秀,問(wèn)了一些與馬克思主義相關(guān)的問(wèn)題,得到了相應(yīng)的解答,獲益匪淺。
如果說(shuō)見(jiàn)大牛咨詢問(wèn)題是“月亮”,那現(xiàn)實(shí)的生活便是“六便士”。
“月亮”很美好,但“六便士”同樣重要。
那段時(shí)間,為了維持日常生活,毛澤東不得不干起了零工。
他為富人闊佬們洗衣服、熨衣服、送衣服,一條龍服務(wù)包圓了,可能比現(xiàn)在的外賣快遞小哥還辛苦。
更糟的是,這種辛苦并不能兌現(xiàn)成等值的回報(bào)。
他雖一月能賺12到15元,但有8塊錢要被消耗在送衣服的車費(fèi)上,實(shí)際到手也就4到7塊錢,老板不會(huì)給一點(diǎn)補(bǔ)貼。
被買辦剝削的生活著實(shí)是難受且不爽的,這段被社會(huì)毒打的經(jīng)歷,讓毛澤東更加認(rèn)識(shí)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價(jià)值所在、以及“無(wú)產(chǎn)者”到底意味著什么。
得了空,毛澤東來(lái)到上海的碼頭邊,送別前往法國(guó)勤工儉學(xué)的湖南學(xué)生。
這些學(xué)生,也是新民學(xué)會(huì)的會(huì)員。
黃浦江上,響起輪船深沉的鳴笛,夾雜著過(guò)往人群的交談呼喊,碼頭工人搬運(yùn)貨物時(shí)產(chǎn)生的撞擊聲,都融化在江面升起的模糊的霧氣之中。
開(kāi)船前,毛澤東召集這幫會(huì)員,在碼頭附近開(kāi)了個(gè)臨時(shí)會(huì)議,統(tǒng)一了共識(shí),并提出了一個(gè)看似樸素,實(shí)則振聾發(fā)聵的口號(hào),與大家共勉:
改造中國(guó)與世界。
2
毛澤東所發(fā)出的這個(gè)口號(hào),其實(shí)反映了他內(nèi)心做事的一個(gè)根本出發(fā)點(diǎn),當(dāng)然不只是說(shuō)說(shuō)而已。
他不僅說(shuō)到,更要做到。
為此,他自求學(xué)時(shí)起,便開(kāi)始進(jìn)行了各種各樣的探索試錯(cuò)。
從溫和的改良派到奮進(jìn)的革命派,看似只是簡(jiǎn)單換了一條路子,這其中要經(jīng)過(guò)多少實(shí)踐挫敗、思維激蕩,難以想象。
面對(duì)這樣的轉(zhuǎn)變,一般人可能就選擇放棄了。
雖然他們可能也對(duì)現(xiàn)實(shí)不滿,但頂多也就是抱怨兩句,雖置身事內(nèi),卻以一種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視角看著周遭的一切,不從自身做起,不想想基于自己現(xiàn)有的能力,能改變些什么,不能改變些什么,然后,就這樣被大時(shí)代裹挾向前,蹉跎一生。
但毛澤東不是,他不僅胸有大志,更要將這大志,努力轉(zhuǎn)換到現(xiàn)實(shí)中。
1920年的那個(gè)夏天,在見(jiàn)過(guò)陳獨(dú)秀,解答了心中的一些疑惑后,毛澤東對(duì)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更加堅(jiān)定了。
回到長(zhǎng)沙后,他聯(lián)系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在潮宗街組建了長(zhǎng)沙文化書社,開(kāi)起了書店,并恢復(fù)了直接解散的湖南學(xué)生聯(lián)合會(huì)。
毛澤東是書社的“特別交涉員”,負(fù)責(zé)外聯(lián)宣傳工作,推廣書社上新的書籍,從現(xiàn)在的角度看,他算是一位新媒體編輯,兼運(yùn)營(yíng)兼營(yíng)銷策劃。
他主推的書目,主要以宣傳馬克思主義學(xué)說(shuō)、俄國(guó)十月革命理論的書籍、《新青年》、《新生活》、《勞動(dòng)界》等進(jìn)步雜志為主,效果還不錯(cuò)。書社生意興隆,一度還在其他城鎮(zhèn)開(kāi)了7家分店。
工作雖然繁重,但卻是毛澤東所認(rèn)同且喜歡的,比起在上海打零工的日子要好太多了,他痛并快樂(lè)著、累并收獲著。
當(dāng)年8月,陳獨(dú)秀在上海成立了共產(chǎn)黨發(fā)起組。
類似咱們現(xiàn)在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組建一個(gè)某正式社群的籌備組。
當(dāng)時(shí)的計(jì)劃是,“預(yù)備在1年之中,于北平、漢口、長(zhǎng)沙、廣州等地,先成立預(yù)備性質(zhì)的組織。”
陳獨(dú)秀十分欣賞毛澤東的才干,他寫信給毛澤東,讓其發(fā)動(dòng)湖南中共小組,算是湖南地區(qū)的負(fù)責(zé)人。
毛澤東沒(méi)讓陳獨(dú)秀失望。
經(jīng)過(guò)緊張籌備,慎重物色,他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黨文件上簽了名,正式創(chuàng)建了長(zhǎng)沙共產(chǎn)主義小組。
彼時(shí),是1920年11月。
有些朋友覺(jué)得,毛主席是在1921年中共一大時(shí)入的黨,但毛主席卻給自己入黨時(shí)間填的是1920年,就是出于組建長(zhǎng)沙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緣故。
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各地的共產(chǎn)主義小組,都陸續(xù)建立起來(lái)。
建黨事宜,開(kāi)始提升日程。
1921年,又是一個(gè)夏天。
前一年的毛澤東,此時(shí)正在上海,做著洗衣送衣的活兒,而今,他則乘船再度來(lái)滬,不必再為日常生活開(kāi)支太過(guò)焦慮,為的是參與一次會(huì)議。
這便是中共一大。
當(dāng)年6月29日,下午6點(diǎn)左右,長(zhǎng)沙小西門碼頭。
毛澤東與友人何叔衡,乘著暮色,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輪。
或許,那時(shí)的他們不會(huì)想到,這次會(huì)議之后,僅僅過(guò)了28年,中國(guó)革命就取得了完全勝利,一個(gè)嶄新的中國(guó),在東方冉冉升起。
這也正常,誰(shuí)也不是神仙,能確切知道未來(lái)事物發(fā)展的走向。
但毛澤東心中有一個(gè)大概估計(jì),他曾對(duì)蕭子升說(shuō),假如我們努力奮斗,有三五十年,中國(guó)革命便可取得勝利。
當(dāng)然,這樣的估計(jì),在當(dāng)時(shí),也沒(méi)什么人會(huì)重視。
畢竟,現(xiàn)實(shí)是殘酷的,有多少人愿意且敢于去思考篤定一個(gè)不確定的未來(lái)?
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一個(gè)沒(méi)啥背景資源的后輩的“囈語(yǔ)”?
當(dāng)毛澤東等人到達(dá)上海時(shí),已經(jīng)是7月初了。
會(huì)議時(shí)間,定在1921年7月中旬。
會(huì)議地址原設(shè)在博文女校,為保險(xiǎn)起見(jiàn),改在了望志路的一棟灰紅磚塊相間的花園住宅里。
這是與會(huì)代表哥哥的府邸。
國(guó)內(nèi)外的共產(chǎn)主義小組,派了13個(gè)人,參加了這次會(huì)議。
他們是:
李達(dá)、李漢俊(上海)
張國(guó)燾、劉仁靜(北京)
毛澤東、何叔衡(長(zhǎng)沙)
董必武、陳潭秋(武漢)
王盡美、鄧恩銘(濟(jì)南)
陳公博、包惠僧(廣州)
周佛海(日本)
除此之外,還有共產(chǎn)國(guó)際的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
與會(huì)的代表大都年輕,出身幾乎都比毛澤東高。
這些,大略是毛澤東給當(dāng)時(shí)代表們,留下的最初印象。
會(huì)議一開(kāi)始,進(jìn)行得相對(duì)順利。
中途遭遇密探的闖入,為了保險(xiǎn)起見(jiàn),余下的會(huì)議,改在了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游船上。
前前后后,整個(gè)會(huì)議開(kāi)了一周左右。
考慮到當(dāng)時(shí)黨員較少,地方組織不很健全,中共大一只組建了三人的中央局,陳獨(dú)秀任書記,張國(guó)燾為組織主任,李達(dá)為宣傳主任,黨的第一個(gè)中央機(jī)關(guān)正式誕生。
毛澤東呢?
他雖然參加了此次會(huì)議,但并非重要人物,會(huì)議上鮮有發(fā)言,也并未進(jìn)入中央核心領(lǐng)導(dǎo)層。
但歷史的有趣之處就在于:
我們對(duì)一個(gè)人所取得的成就和評(píng)價(jià),并不是看一時(shí),而是縱觀一生,綜合評(píng)價(jià)。
金一南教授曾做過(guò)一個(gè)統(tǒng)計(jì):
“當(dāng)年參加中共一大的一共13人,平均年齡27歲,都是青年人。
這些人里面,1人脫黨,1人被開(kāi)除,3人叛黨,2人投靠了日本人,也就是說(shuō)一半以上都已半路放棄。
除開(kāi)犧牲的幾個(gè)人,真正堅(jiān)持到底的不過(guò)兩三個(gè)人。
而毛澤東正是其中之一。”
起點(diǎn)低怎么了?
背景弱怎么了?
資源少怎么了?
如果既有的現(xiàn)實(shí)不能立刻改變,那就選擇承認(rèn)。
但承認(rèn)不是認(rèn)命,而是為了建立一種客觀現(xiàn)實(shí)的理性態(tài)度。陷入無(wú)休止的抱怨和持續(xù)性的躺平擺爛,沒(méi)有任何正向的意義。
社會(huì)依舊運(yùn)轉(zhuǎn),你卻離自我的真正蛻變?cè)絹?lái)越遠(yuǎn)。
長(zhǎng)期來(lái)看,我認(rèn)為,一個(gè)人只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只要不斷積極努力奮斗,不斷適應(yīng)新的發(fā)展情況,那么,這個(gè)人,大概率會(huì)邁上新的人生臺(tái)階,達(dá)到新的人生高度。
既能實(shí)現(xiàn)自我價(jià)值,又能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志同道合之人,創(chuàng)造更大的價(jià)值。
聽(tīng)起來(lái)似乎很雞湯,但現(xiàn)實(shí)的人生突圍邏輯,可能大略就是如此,沒(méi)那么復(fù)雜。
我們有毛主席作為榜樣指路,何愁找不到自發(fā)的行動(dòng)契機(jī)和無(wú)窮的精神源動(dòng)力呢?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yùn)行與維護(hù)。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