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舊體詩詞大家的毛澤東
王國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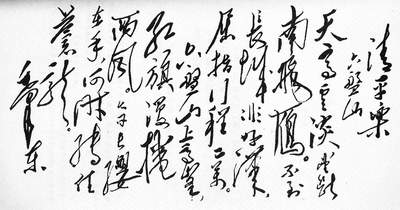 |
縱觀毛澤東全部的50首詩詞作品,從時間上來分,解放前的31年(1918—1949)創作了27首;解放后的15年(1950—1965)則創作了23首。比較而言,創作率明顯是后期高于前期。從創作第一首七古《送縱宇一郎》的1918年,到他“正編”中最后發表《賀新郎·揮手從茲去》、七律《吊羅榮桓》、《賀新郎·讀史》三首詩詞的1978年,前后剛好是60年的歷史跨度。而這60年,卻正好是中華詩詞逐漸走向衰落的60年。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我國有古典詩詞的悠久傳統;在1978年三中全會之后,則又有中華詩詞的復蘇和振興。毛澤東的詩詞,恰恰在這60年中獨樹一幟,頑強不息,以量少而質高的50首詩詞作品,用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無論在思想上或者內容上,都為我國當代的詩歌藝術史增添了無與倫比的光輝的一頁。
1957年元月,剛剛創辦的《詩刊》準備發表毛澤東的幾首詩詞。主編臧克家向毛澤東寫信征求意見,毛澤東就給臧克家回信道:“這些東西,我歷來不愿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又說:“詩當然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就是這封本來非常正常的私人信件,卻因為它的發表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一生沒有自己系統的詩歌理論。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寫給臧克家等人的幾封信,后來才會被人誤解甚至歧解,以至招來不少人的疑慮和責難。尤其是對他在信中所表達的一些詩詞理論,更使一些人把五四以來中華詩詞的逐漸衰落,自覺不自覺地與毛澤東的名字聯系在一起。
我們首先需要搞清的一個問題是:毛澤東當時寫信的真正意圖是什么?他還有沒有更多、更全面的詩詞理論呢?
先讓我們注意一下毛澤東的另外兩封私人信件:
“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志一閱,看有什么毛病沒有?加以筆削,是為至要。”(1959年《致胡喬木》)“你叫我改詩,我不能改。因為我對五言律,從來沒有學習過,也沒有發表過一首五言律……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如你會寫自由詩一樣,我則對于長短句稍懂一點。劍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學律詩,可向他們請教。”(1965年《致陳毅》)
無須多言,我們從這兩封信中讀出了什么呢?謙遜!作為一代偉人,毛澤東能夠如此虛懷若谷,坦誠相見,不正是毛澤東風格的自我謙辭嗎?更何況,這句話的下邊,還有一句“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么特色”的補語呢!同時,毛澤東還在信尾特別注明:“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意義已經是如此明確,怎么偏偏還會被人誤解呢?再讓我們參考一下毛澤東自己的解釋吧:1965年夏的一個夜晚,武漢市文聯主席梅白曾在武昌向毛澤東請教:“主席為什么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呢?”當時,毛澤東躺在一個藤椅里,仰望著夜空上的點點繁星回答:“那是針對當時的青少年說的。舊體詩有許多講究,音韻、格律很不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的思想,不如新詩那樣自由。”“我不勸青年人學它,是因為青年人要學的東西,在格律之外還多得很。”這里需要研究的,就只有“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問題了。從今天看來,以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毛澤東的說法確有其一定的道理:第一,國家初創,百廢待興,廣大青年需要學習的新生事物實在太多了。第二,從詩歌發展的情況來說,擺脫了格律束縛的五四新詩,與破舊立新的時代精神相呼應,自然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時尚。第三,作為一種特殊的詩歌體裁,詩詞難以直接為國家的經濟建設服務。第四,詩詞本身確實也存在一定的技術難度。所以,毛澤東在《致胡喬木》的信中又談到:“詩難,不易寫。經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這是詩人內心甘苦的自白。如此觀之,倘若毛澤東當時大力倡導青年人去學寫舊體詩詞,對于一個開國領袖來說豈不有悖于輕重緩急的情理?而且,正是因為毛澤東自己的謙遜胸懷,他更不會不顧大局而倡導個人無比喜愛的詩詞了。
但是,問題的關鍵卻并不在此,而在于他僅僅說“不宜提倡”,并沒有說“不準提倡”;僅僅說“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并沒有說“不宜在所有人中提倡”;僅僅是詩人之間的一封私人通信,決不是他所倡導的文藝政策……所以,毛澤東又對梅白說:“但另一方面,舊體詩詞淵遠流長,不僅像我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們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造,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怨而不傷,溫柔敦厚嘛!”(梅白《回憶毛澤東論詩》)
毛澤東從來也沒有強加于人;而毛澤東在個人通信中的自我謙辭,卻被人意外地誤解和放大了,問題是如此的簡單卻又如此的復雜。
毛澤東非常喜愛中華(古典)詩詞,并且用自己的偉大實踐繼承并發展了這種優秀的傳統詩歌形式。但是,他卻從不因為自己的個人愛好去影響別人的愛好。臧克家在《毛澤東同志與詩》一文中論述說:“他(即毛澤東)自己寫舊詩,但不主張青年人學寫舊詩。他對新詩看得不多,也從來沒寫過,但他主張現在寫詩應以新詩為主。這種不憑個人意志與偏好的科學態度,大大值得我們學習。”從這一點來說,恰恰又反證了問題的另一方面:毛澤東對自己不感興趣的新詩尚能如此寬容地提倡,那么對于自己極感興趣的舊詩會大加限制嗎?很顯然,在毛澤東的內心深處,對舊體詩詞的依戀情結還是十分強烈的。這不僅表現在他自己幾乎貫穿一生的創作實踐中,而且也反映在他的多次談話中。
還是在與梅白談話時,毛澤東曾經這樣說:“把詩分成新舊,是不科學的。”“就我的興趣說,則偏愛格律詩……我不喜歡新詩,也不反對人家寫新詩。豆腐炒青菜,各人心里愛嘛。”他還特別強調說:“格律詩和新詩,都應該在發展中改造。”“格律詩是打不倒的,除非有更好的東西代替它。至于新詩,也打不倒,青年人喜歡嘛。”于是,這就又有了毛澤東“新舊詩并存”和“都應該改造”的理論。
那么,到底應該如何改造呢?對此,毛澤東又多次這樣闡述:“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有可能從民歌中吸取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致陳毅》)“新詩的作者,要學習格律詩的含蓄、凝練……格律詩要學習民歌的時代色彩、鄉土氣息和人民情感……新詩、格律詩、民歌,會不會取長補短,發展成為中國式的真正的新詩?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梅白《回憶毛澤東論詩》)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還曾發表這樣的講話:“我看中國詩的出路恐怕有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方面都要提倡學習,結果要產生一個新詩。現在的新詩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當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統一。”(宋貴侖《毛澤東與中國文藝》)
毛澤東的詩詞理論還不夠明確嗎?
在一段時間里,總有人自覺不自覺地將新中國成立以來詩詞發展逐漸衰落的責任全部歸咎于毛澤東的“不宜提倡論”,甚至對毛澤東的詩詞作品也進行隨意的臧否。這里,我們在澄清是非的基礎上,希望重新認識毛澤東的詩詞觀和他在現當代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充分肯定他所取得的藝術成就,這對于真正地繼承和發展中華詩詞事業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而對于客觀公正地評價毛澤東和他的詩詞藝術,也具有著重要的社會和歷史意義。(來源:中華讀書報)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