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批判的若干問題(中)
【編者按】
以下試圖通過爭鳴方式回答兩個基本問題:(1)什么是辯證法?(2)什么是科學抽象法?第一個問題的簡明答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辯證法看成這樣的方法規(guī)定:既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同時也是“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歸根結底,是“唯物論上的辯證法”和“辯證法上的唯物主義”的規(guī)定性合成。第二個問題則鎖定于“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統(tǒng)一的工作路線,一句話,它強調沒有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就不會有“科學抽象”。社會主義批判說到底啟動的是“勞者”的品格——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建構品格,夯實的是勞動二重性實踐邏輯的方法地基。從學理上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時代重建是對教科書科學抽象法“解構行動”的引領和超越。
謹以此文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暨列寧誕辰150周年!

辯證法工作原像問題
什么是批判?一曰高度,二曰尋求規(guī)律,三曰反對庸俗。針對保爾·巴爾特的“經濟唯物主義”,恩格斯提出辯證唯物主義方法意蘊的“歷史合力論”,就是從歷史高度上,從《矛盾論》和《實踐論》結合意義的規(guī)律(規(guī)定)的探求上,對“庸俗決定論”進行了徹底反駁。恩格斯之后,較為完整繼承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革命批判事業(yè)的人是列寧。真理必須走向現(xiàn)實,然則唯物史觀在列寧那里,第一次“辯證法范疇”化了,既從形式也從內容考察唯物史觀的諸構成要素的發(fā)展。這意味著“批判”的開始植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意義本體,成為行動規(guī)定。
【注:關于批判,哈貝馬斯擁有中肯的意見:“只有這個大陸組織(即歐盟)有能力控制住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我從沒有停止批判過資本主義,但我也一直清楚,不痛不癢的診斷是不夠的。我不是那種漫無目標的知識分子。”盡管如此,盡管“康德+黑格爾+啟蒙+祛魅的馬克思主義”的哈貝馬斯批判主義可部分填充和彌補《資本論》在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不在場”,但它根本缺乏“改變世界的現(xiàn)實性和力量”,——反過來看,列寧所繼承的批判規(guī)定是完整的,即“資本主義批判”和“社會主義批判”的工作統(tǒng)一。這種前后推進、繼承發(fā)展和在“克服認識障礙”之后的不斷破浪前進的馬克思主義學術工作關系告訴我們:理論批判從來都是人類思想進步的活水、社會發(fā)展的源泉。】
恩格斯指明: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作科學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密納發(fā)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然則社會主義規(guī)律研究正逢其時。今天的群眾已經被教育了——就像列寧在1918年所說:那些由于只能讀到滿篇都是造謠誣蔑的資產階級報紙而不了解俄國情況的工人,現(xiàn)在也開始明白了。馬克思說“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然則,“對于辯證法需要認識到,其確實是一個全體方法的規(guī)定。也是因為對這個工作規(guī)定的肯定,馬克思堅持把《資本論》視為辯證法在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成功的運用。”思維科學是從辯證法中生發(fā)出來的規(guī)定,但不限于辯證法的本體,是從思維形式的運動和構造方面引領正確的知識生產,——這是它的方法論學科內涵的準確定位。亦即可以說,“馬克思堅持了從‘對象思維’出發(fā)進行科學研究這一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工作立場,堅持把科學抽象法作為‘思維原則’的規(guī)定,而不是邏輯推理的手段,主張在‘思維學’下闡述范疇的邏輯學、知識論。”【注:許光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兼對生產一般與資本一般機理關系的考訂》,《 經濟縱橫》2019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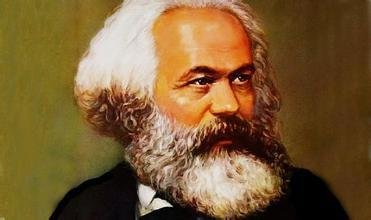
第二種批判
接續(xù)的第二種批判是第一種批判工作的深化,用意在于指出邏輯本體——基于存在和基于知識的本體論推導——的弊端,指示出兩種方法的內在聯(lián)系。指明本體論邏輯推理的實質性危害:若與科學抽象法工作對接,則導致唯辯證法之主義;若既和科學抽象法,復與資產階級知識論工作對接,則進而導致唯科學之主義。這兩種工作情況中,將抽象法換成物象法,問題的實質是一樣的。前一者試圖使辯證法操程化,沉迷于路線圖的規(guī)劃;后一者試圖使辯證法科學化,熱衷于純然構圖意義的知識。可是,所謂實體運動和實體構造的研究對象的考問,既不是說要進行以實體為基礎的單一方向的從形式到形式的疊加運動,也無意進行實體-形式的線性對偶的認識活動。毋寧說,這是實體在歷史運動中構造自身。這個實體按照本性只能是社會實體,乃是社會發(fā)展實體和社會實體之生成運動。生產方式按照規(guī)定性是支持生產關系-交換關系運動的骨骼形態(tài),即時間發(fā)展方面的規(guī)定;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是運動的內容和運動肌體的組織構造形式,即空間發(fā)展方面的規(guī)定。
馬克思創(chuàng)作《資本論》歷程已經表明,他稱為“我的辯證方法”的,實際是歷史和實踐化批判方法,而并不是什么唯科學的工作主義和唯辯證法的工作主義。這樣,即需要對這些研究活動進行明辨,審問其邏輯推理程序是否恰當以及相應工作是否合法。例如說: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從起點上就包含著對價值范疇自身的規(guī)定,因此,馬克思從未打算而且也沒有必要“證明”他的價值及其規(guī)律的規(guī)定性。馬克思關注的是,給定了他的分析框架,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如何在這一個框架下運行的。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從一開始就被很多反對者誤解了……在李嘉圖看來,勞動時間確定價值這是交換價值的規(guī)律……由于他沒有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他的價值理論并不帶有“實體-形式”這樣的“對偶”。在李嘉圖那里,價值范疇只是一個作為產品的核算框架或者作為“影子價格”進行產品總量表征……暗喻了李嘉圖谷物模型的思想起源……(馬克思)堅持:只有同時說明了價值的“內在實體”和“外在形式”,價值的概念才能得以完整地說明。這帶有濃重的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的個人特點……因此,與龐巴維克和薩繆爾森所理解的不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是由一對不可分割的對偶范疇所組成的整體……價值實體是一個理論預設,它不是為了解釋商品交換的現(xiàn)實關系,而是為了給出一個客觀實在的“統(tǒng)一實體”,并且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的現(xiàn)實關系只不過是這一個“統(tǒng)一實體”的運動表現(xiàn);而“價值形式”則是這個抽象實體在現(xiàn)實關系下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一個由抽象“價值實體”和具體“價值形式”組成的高度對偶體系,它表現(xiàn)了一個事物“內在實體”和“外在表現(xiàn)”的辯證關系:價值實體定義了價值形式的內容,價值形式在具體歷史條件下表現(xiàn)著這一內容。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考察都是建立在這一對偶體系上的,單獨考察任何一方都不能正確而完整地把握馬克思的理論體系。而其中建立在馬克思哲學思想上的“價值實體-價值形式”對偶結構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古典勞動價值論的決定性區(qū)別,也是研究和發(fā)展馬克思經濟學必須充分認識的問題。【注:裴宏:《實體與形式對偶的勞動價值論》,《政治經濟學評論》2012年第1期。】
劉召峰博士在文章中并沒有發(fā)表對經濟形態(tài)社會發(fā)生問題的看法,事實上,他對這一發(fā)展規(guī)定尚沒有進行專門性研究。似乎對此存而不論。看來,他并不了解勞動二重性指示了生產關系的生成運動,也并不準備把它視為生產研究對象規(guī)定的一個總裝置。
裴宏博士對這個問題表現(xiàn)出同等程度的漠視。因為沒有對抽象勞動的形成進行追溯,并根據(jù)這一規(guī)定展開系統(tǒng)性探究,余下的任務就只能由本身顯得干癟的敘述承擔,認定“勞動價值論從起點上就包含著對價值范疇自身的規(guī)定”。這是一個應然的判斷,只“帶有濃重的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的個人特點”。依據(jù)文本考據(jù)的語義解讀,似乎,“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高度自洽的”,“價值范疇是‘分析的’而不是‘經驗的’”,以及僅來自分析起點——是起點的演繹結果;仿佛:馬克思主張“勞動價值論”,“不需要建立在任何特殊的社會條件下得以成立。”因為,劉召峰博士也建議了:“馬克思運用勞動二重性學說所考察的其實就是‘勞動的普遍與特殊’。普遍就一切勞動都是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耗費,而且必然是在一定時間上的耗費而言,勞動是抽象勞動,或者說勞動具有其抽象性;特殊就一切勞動都是勞動者的體力和腦力在一定形式上的耗費而言,勞動是具體勞動,或者說勞動具有其具體性。”這好像是存在固有的性質,是勞動本身的性質。這里沒有談到勞動方式的特殊規(guī)定,沒有對特定生產的指涉,沒有提及和說明任何產生關系的歷史生長運動,并且,類存在和個例的存在照例都是一樣的。存在者混同在它的存在規(guī)定中了。
因為經驗只能是個體(單個組織或個人)的,價值范疇仿佛輕松越出了個人主義;又因為馬克思說過抽象是唯一可以依憑的分析工具,存在者就變身為抽象。經過裴宏博士的處理,價值代表了語言的沉默,仿佛那個愚蠢的寓言:人總會在暗處尋找失物,忘記了明亮所在。與此同時,勞動(抽象勞動)又被指認是普遍的,仿佛在說另一個更加愚蠢的寓言故事:人總是在亮處尋找失物,忘記了“暗處”。把存在和存在者完全隔開,忘記暗處同樣是客觀存在,而且是同亮處結合在一起整體工作的存在規(guī)定,忘掉了它們的內在聯(lián)系。完全文本化的處理引誘著用以上同種的方式分別尋找“馬克思”,便于各取所需。答案只會分別從“價值幻覺”和“格式塔幻覺”身旁穿過。我們卻從來無法超越它們。這或許是人的行為固有的“某種惰性”。它具有持久性,但不會是天然有的,如果是那樣的話,仿佛真的成了“心理學”。語言是通過類存在的行動產生,又由個體予以識別的一種認知活動。它同樣是一種實踐——理論的、認識的活動。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力,廣義地,主要針對語言工作現(xiàn)象而言;而通過排除實驗科學的認識障眼法,將語言生產和認識生產統(tǒng)一起來。從歷史規(guī)定方面創(chuàng)造了范疇生產上的真境界。存在者(規(guī)定)從中脫身而出。現(xiàn)在,它認認真真地來到面前,要求我們指出邏輯操作的非法性,從而在這里,它甚至直接要求進行歷史操作。
所以我們要說,馬克思從物質生產和它所包含的關系方面界定二重性,用語性質絕不應歸于寓言式的說教,而應歸于歷史語言。任何把它重新當成科學語言的體例的做法勢必跌入這種或那種形式的語義學,進行直接或間接的解釋學宣揚。因此,所謂馬克思二重性語言,并不在于解釋世界,而在于依循歷史發(fā)展情勢批判世界、改變世界,在于歷史實踐本身。用語性質的核心之處如前所述,在于指示大寫生產規(guī)定,用旨是探明歷史與認識的內在結構。由此可見,勞動二重性是發(fā)生學的工作邏輯:既是認識裝置,也是實踐裝置,是內在剖解經濟形態(tài)社會的裝置,同時必然是歷史方法論。這些裝置直接抵減了資產階級科學用語的工作語義,整體產生出革命化批判的實踐語境效果。
劉召峰博士將勞動二重性和物象二重性相提并論——作為解釋共同體,認為它們都是古典經濟學在說自己,這依然是約定主義和假設思想在作祟。在這里,資產階級解釋學作為罕見的一種邏輯力量的表現(xiàn)而在場。繼之,裴宏博士關于“勞動價值論是一個獨立于具體經濟現(xiàn)象的一般框架……來自對現(xiàn)實高度抽象提煉的思辨和內省”之申論,也實在唬人的很,是解釋學作為罕見的科學展示力量的工作登場。但實體和形式真的是“對偶的認識”嗎?深層次看,這種認識恰恰是資產階級工作者所普遍采用的方法,而且不是別的,正是所謂的純粹理性批判方法的實質,即“實質是指伽利略和牛頓等人所確立、被當作精密科學工具的……方法。這樣一來,人們對客體的認識就只限于從數(shù)量以及數(shù)和形的關系的形式方面去把握,而它們的內容和本質則被推到了不可認識的彼岸領域。”其實,“這就是盧卡奇反復批評的那種經驗(現(xiàn)象)直觀和形式理性主義的方法。”【注:孫伯鍨:《盧卡奇與馬克思》,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68頁。】

這是在直觀唯物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方法支配下的“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破除這種概念結構和認識方法的工作路徑是堅持從歷史出發(fā),在恢復了“內容和本質”的工作場域中最后滌蕩干盡形式理性主義。
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即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刻開始。進入交換的產品是商品。但是它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在這個物中、在這個產品中結合著兩個人或兩個公社之間的關系,即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這里,兩者已經不再結合在同一個人身上了。在這里我們立即得到一個貫穿著整個經濟學并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頭腦中引起過可怕混亂的特殊事實的例子,這個事實就是: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xiàn)。誠然,這個或那個經濟學家在個別場合也曾覺察到這種聯(lián)系,而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這種聯(lián)系對于整個經濟學的意義,從而使最難的問題變得如此簡單明了,甚至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xiàn)在也能理解了。【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4頁。】
對于恩格斯這段話,且看奚兆永教授如何說:
有一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這就是,既然“交往關系”和“生產關系”具有相同的含義,為什么在“生產關系”之后還要加一個“交往關系”呢?我理解,這兩個術語的基本的含義雖然相同,但在強調的方面和色彩上還是有不同的。生產關系不能離開生產過程,用恩格斯的話說,“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xiàn)”,但是,從實質上看,這些關系“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著眼于前者,我們可以說它是“生產關系”,著眼于后者,它就是“交往關系”。另外,我們對于德語的und似也不必理解得太死。und當然是“和”或“與”的意思,但是由und連接的前后的詞語卻并不完全是并列的關系,其后面的詞語對前面的詞語實際上也含有遞進的意思……如果有這樣的認識,那么我們對“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理解也就不會感到怎么困惑了。【注:奚兆永:《申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答胡世禎、郭冠清并論“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的翻譯》,《海派經濟學》2004年第2期。】
實體運動和實體構造整體形成了對研究對象規(guī)定的限定,并非實體構造本身;實體構造相反地是隸屬于實體運動性質的,因而不是純邏輯構造。裴宏博士似乎并沒有理會這一點。他談到,“第一卷中,馬克思給出了‘價值實體’的概念,在第三卷則給出了‘價值實體’在充分發(fā)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所表現(xiàn)出來的‘價值形式’,即生產價格。而著名的‘轉型問題’則是對‘價值實體’到‘價值形式’轉換的邏輯說明。”大概這樣說,是為了把第一卷的《價值形式》看作一純邏輯討論。但是,如果忘了剩余價值生產對于一般價值生產的歷史置換,是根本無法弄清楚市場價值如何轉化為生產價格的。這是實體-形式的歷史逐步發(fā)展過程,是實體-形式從生活過程角度來看的資本主義實現(xiàn)問題。可見,實體-形式-生活的整體生長關系是價值轉化問題的理解基礎。其實在這方面,恩格斯說的更為明確清楚。他說,為什么必須把“邏輯的方式”歸為“歷史的方式”呢?因為,“我們采用這種方法,是從歷史上和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簡單的關系出發(fā),因而在這里是從我們所遇到的最初的經濟關系出發(fā)。我們來分析這種關系。既然這是一種關系,這就表示其中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lián)的方面。我們分別考察每一個方面;由此得出它們相互關聯(lián)的性質,它們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現(xiàn)了需要解決的矛盾。但是,因為我們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們頭腦中發(fā)生的抽象的思想過程,而是在某個時候確實發(fā)生過或者還在發(fā)生的現(xiàn)實過程,因此這些矛盾也是在實踐中發(fā)展著的,并且可能已經得到了解決。我們考察這種解決的方式,發(fā)現(xiàn)這是由建立新關系來解決的,而這個新關系的兩個對立面我們現(xiàn)在又需要展開說明,等等。”【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3-44頁。】
以實體-形式(整體轉化和母子過渡的工作關系)為基礎的生活形式獲得:既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特殊規(guī)定的發(fā)生前提,也是有關于這個規(guī)定發(fā)展的說明過程。認識到這一點,也就不會導致對馬克思生產價格理論“意義限度”的指責,說什么:“資本主義早已跨過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全球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在這樣的時代里,中小資本的流動越來越受到大資本的限制……一般利潤率規(guī)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過時了,或者說僅僅處于一種從屬地位。在這樣的時代,具有更重要理論意義的不是馬克思的生產價格理論,而是其關于壟斷和‘國際價值’的論述。”【注:劉召峰:《“從抽象上升到具體”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以“勞動的耗費、凝結與社會證成”為中心線索的解讀》,《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2期。】
生產價格→生產價格形式→壟斷價格(以壟斷為經濟內容的市場價格)的發(fā)展不是摒除部門間的競爭形態(tài),恰恰相反,是要動用這個理論說明意義限度問題;在“壟斷競爭”(以壟斷為手段和形式的資本競爭)條件下,指明它的實質所在:為什么生產集中、資本集中和以金融控制為核心內容和依托的壟斷一定會發(fā)展為虛擬資本主導的社會生產,乃至伴隨著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生成運動序列,“金融機器”控制體系(意味著由金融寡頭集團集中控制社會機器體系的信息控制中心)一定能夠形成,一定能夠擴展至全球領域。因為壟斷不是改變競爭的內容,只是改變其作用形式,即它通過改變平均利潤的形成過程和在外表上的表現(xiàn)形態(tài),使資本競爭具有越來越深化發(fā)展的內容和形式。而壟斷(資本)之成為經濟生活的領頭羊對資本家的治理邏輯來說,則又不過是行業(yè)層面的治理→國家層面的治理→全球層面的治理這一“自發(fā)秩序”之擴展過程。歸根結底,壟斷不改變競爭的基礎性作用,更不會改變剩余價值生產的基本狀況。

第三種批判
盡管我們說明了勞動二重性的歷史發(fā)展根據(jù),但人們按捺不住好奇心,依然要問:馬克思的勞動范疇究竟從何而來?禁不住地要做一番知識梳理。
我們不禁要問,馬克思為什么沒有對生理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與經濟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進行區(qū)分?筆者認為,這恰恰是由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設定即“現(xiàn)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這種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所決定的……區(qū)分生理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與經濟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本身就是多余的工作,因為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下,生理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已經轉化為經濟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生理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本身已經從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視域中“自然地”消失了!或者說,面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生理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與“經濟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被“壓縮”在同一個“抽象勞動”范疇之中……因此,馬克思在選擇邏輯起點的時候,并沒有選擇最抽象的“生理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而是選擇作為商品價值實體的“經濟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因為這才是闡明資本的直接的邏輯起點。然而,從嚴格的邏輯分析來看,將“勞動一般”“勞動一般這個抽象”“抽象一般勞動”和“抽象人類勞動”等概念等同于經濟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并不是無條件的……“勞動、勞動一般、直截了當?shù)膭趧舆@個范疇的抽象,這個現(xiàn)代經濟學的起點,才成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所以,這個被現(xiàn)代經濟學提到首位的,表現(xiàn)出一種古老而適用于一切社會形式的關系的最簡單的抽象,只有作為最現(xiàn)代的社會的范疇,才在這種抽象中表現(xiàn)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這一段幾乎所有探討抽象勞動概念的學者都曾引用過的話,恰恰表明了生理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向經濟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轉化的社會經濟條件以及這種轉化的歷史必然性。【注:任洲鴻:《再論馬克思的抽象勞動概念》,《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5期。】
這里同第一種批判一樣,把勞動二重性降低為物象二重性的層次來理解,認為二重性的功能只在于作為表現(xiàn)“一般永恒”規(guī)定的基礎,爾后更為強調了包含在后者當中的社會規(guī)定。作者先生的一個取得進步的特點是:指責物象二重性,指責把勞動二重性混同為物象二重性,即更加強調商品二重性到資本二重性的發(fā)展的認識重要性。所以為了避免“思想折中”,就得鏟除馬克思意義的勞動二重性,把它歸結為生理學說,然后從這種學說中走出,尋求真正的雇傭勞動學說,即經濟學意義的抽象勞動學說。然而所說的“經濟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乃是特指簡單勞動范疇。因為,抽象勞動本身(勞動的抽象存在)并不能算作是任何的范疇,作為抽象本體,我們前面已經指出,僅是對商品生產關系這一存在者類型的工作考問。可見不像前兩種批判,第三種批判是關于存在和范疇工作關系的,換言之,工作是直接落在科學辯證法框架之內了。出發(fā)點是邏輯起點,而有了“生理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的提出與質疑。即認為直接的起點必須是范疇,而不能是存在,否則易于受到理論攻擊:
例如,讓我們假定能量是系統(tǒng)中的一項投入物。能量將進入大多數(shù)商品的生產,并且,通過家庭取暖等,也進入勞動力本身的生產。每一種商品,包括勞動力在內,將含有一定數(shù)量的“具體化能量”。“剩余能量”將是來自能量部門、進入經濟組織其余部分的凈能量。利潤受剩余能量的限制,猶如受剩余勞動的限制一樣。這樣我們可以毫無誠意地編造一套“能量價值論”。
如上指出,勞動二重性“與生俱來說”事實上也就屈服于這套觀點了。因為,它無法反駁這一論證:
在無論什么情況下,“具體化勞動”的數(shù)量總是根據(jù)特定的工藝計算,包括所使用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所以,“具體化勞動”的數(shù)量在資本主義以外的其他生產方式中也可以計算,只需勞動是同質的,或者可以有辦法把它折合為一種共同的標準。工業(yè)技術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中可能不同,而各自的具體化勞動的數(shù)量,卻仍可以分別計算。所以,“具體化勞動”的概念,在社會上不是對資本主義特殊的;這一概念是有關生產力的技術狀態(tài),而不是有關生產關系。
并且按照實體與形式對偶說,比照著“語義對偶”的存在性,所以就應該說:
具體化勞動價值的概念,對理解社會的生產過程既不必要,也不夠用……實際上,這種概念還不僅僅是不必要,而是對科學思想的一種障礙。【注:霍奇遜:《資本主義、價值和剝削——一種剝削理論》,于樹生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第124-135頁。】
演化學家霍奇遜的意思是,實際上,沒有足夠的理由或根據(jù)支持人們把勞動中的抽象和具體(規(guī)定)分開,而將社會度量的尺度職能單獨賦給抽象勞動。事實上,也不可以這么做,勞動只能作為“具體化勞動”。這就是引文作者對“馬克思的抽象勞動”(其所說的“生理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產生擔憂的理由所在了。馬克思認為,抽象勞動是商品生產方式和商品生產關系的合一規(guī)定,集中反映商品經濟形態(tài)研究對象之生成性,展示生產關系存在者類型之特殊。因此由存在上看,勞動的生理耗費活動和經濟關系的蘊涵必然是統(tǒng)一的,甚至說是同一個工作規(guī)定,這就從抽象勞動方面獲得了唯物主義基礎的規(guī)定。換言之,這里并不存有生理耗費和經濟的意義區(qū)分,它們均應當視為特定社會存在規(guī)定。為什么呢?
只要我們考察的不是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而是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不是孤立的商品生產過程,而是全社會范圍內不斷進行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情況就不同……他一舉兩得。他不僅從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東西中,而且從他給工人的東西中獲取利益。用來交換勞動力的資本轉化為生活資料,這種生活資料的消費是為了再生產現(xiàn)有工人的肌肉、神經、骨骼、腦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在絕對必要的限度內,只是把資本用來交換勞動力的生活資料再轉化為可供資本重新剝削的勞動力。這種消費是資本家最不可少的生產資料即工人本身的生產和再生產。可見,工人的個人消費,不論在工場、工廠等以內或以外,在勞動過程以內或以外進行,都是資本生產和再生產的一個要素,正像擦洗機器,不論在勞動過程中或勞動過程的一定間歇進行,總是生產和再生產的一個要素一樣。雖然工人實現(xiàn)自己的個人消費是為自己而不是為資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變化。役畜的消費并不因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為生產過程的一個必要的要素。工人階級的不斷維持和再生產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條件。資本家可以放心地讓工人維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實現(xiàn)這個條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個人消費盡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圍之內,這種做法同南美洲那種強迫工人吃營養(yǎng)較多的食物,不吃營養(yǎng)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為,真有天壤之別。【注:《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60-661頁。】
最終,情況可以顯見了:“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轉化為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yè)中完成的。”【注:《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87頁。】
這是假設?歷史假設嗎?假設并不是為了論證的方便而略省步驟或研究條件之假定,其根本是虛假的。這里顯然不會是。但引文作者會說是。“馬克思之所以得出這種近乎極端情況的理論判斷,與其暗含的重要假設密切相關,即雇傭工人與科學知識與其他勞動條件一樣,都始終處于一種‘絕對的分裂或分離’狀態(tài),這個理論假設與其在《資本論》中明確表示始終把‘把各種勞動力直接當作簡單勞動力’的理論假設是內在一致的……可見,馬克思所理解的勞動力商品的再生產,實際上將勞動者掌握、占有和積累知識生產要素的可能性排除了,從而將知識生產要素排除在勞動力概念之外。”智力存放方式的改變才是資本支配勞動的條件和權力。由于不能把占有看作實在的歷史財產因素,自然形成這種認識:“馬克思認為勞動力的表現(xiàn)即‘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但作者先生旋即說,“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認為,雇傭工人與科學知識的‘絕對分離’是內生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經濟特征,只有在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tǒng)治的基礎上,雇傭工人與科學知識的‘結合’才有可能實現(xiàn),即‘工人階級在不可避免地奪取政權之后,將使理論的和實踐的工藝教育在工人學校中占據(jù)應有的位置。’”【注:任洲鴻:《知識積累與勞動力資本化:一個基礎理論模型》,《經濟評論》2013年第4期。】
引文作者實際看到了勞動過程的歷史運動,只不過力圖把它當成假設的變動。從勞動力商品到勞動力資本化似乎是工人與科學知識的“分離”到“結合”,似乎就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的運動。
【勞動力資本化注:是說社會存在運動嗎?顯然不是,說的是假設知識的變遷。把馬克思的抽象勞動硬說成“范疇”,是方便把真正的抽象規(guī)定擠出去,便于邏輯演繹和知識推導。】
所以,它要與“生理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區(qū)劃開,撇開對生理耗費活動的歷史研究,并且要采取斷然否認人們對自己生理活動的占有是始源的財產關系規(guī)定的認知方式。但是,歷史上畢竟存有“生理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向經濟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轉化”,就要迫使“自然”(客觀實體)全部化為“社會”(經濟形式)。可那樣分立的話,圖能援引假設為據(jù)了。例如,霍奇遜裸露地說:“自然主義的跡象,以及一種聯(lián)系在一起的機械論的觀點,仍然可以在《資本論》中看到。這些東西的來源之一是馬克思所未能發(fā)展的一種‘財產論’。在這方面他的著作與斯密和李嘉圖的相似。像他們一樣,馬克思由于采用勞動價值論,無意中堵上了自己尋求適當?shù)呢敭a論的途徑……沒有一種關于財產的學說,他反對資本主義,就不得不尋求一種不同的理論根據(jù)。”霍奇遜囿于沒有能力認識問題,只得歸責于“馬克思身上的自然主義”,因為他非要把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的財產分割說成是純自然主義導向的。
【注:前面交代,這是指明工人勞動時間在財產上的兩種狀態(tài):資本家的絕對財產和資本家的相對財產,分別由絕對和相對的剩余價值生產說明。毋寧說指明了: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tǒng)一運動是工人淪為自己勞動的非占有者(非資產者或無產者),相反,資本家成為他人勞動的占有者(資產者)的經濟根源,也是工人與科學知識“絕對分離”的歷史根源。他們同科學知識的重新結合,使生產知識成為工人自己的知識;這一發(fā)展過程是對勞動力商品的規(guī)定加以整體揚棄的運動,并不能通過所謂的直接資本化的途徑實現(xiàn)。另外,關于這個問題的分析已至少能夠說明:所謂知識,也并非純然技術狀態(tài),其作為生產要素具有特定的社會經濟含意;所謂工人同知識的“結合”,既非自然的狀態(tài),也不會是物質發(fā)展的單向度的抉擇,而受制于整體概念的勞動生產方式的發(fā)展。可見,沒有財產關系的歷史性變革而空談“勞動力資本化”,在認識上也是極為有害的,也是對基于生產剝削的財產分割概念的一種有意識的模糊。】
就硬著頭皮說:“這種以勞動作為價值和實際社會成本的衡量標準的自然主義的概念,常常出現(xiàn)在馬克思主義的隱喻里,所謂工作日分為工人‘為資本家工作的時間’(即剩余勞動)和工人‘為自己工作的時間’。”【注:霍奇遜:《資本主義、價值和剝削——一種剝削理論》,于樹生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第150-151頁。】
勞動耗費具有客觀性,“這是一個生理學上的真理。”消費勞動不過是消費一定的生理形式,不過是耗費生理的社會活動。然而,不變的真理規(guī)定也只是耗費活動本身和耗費活動的對象,至于耗費方式本身和耗費活動或方式的等同性則從來不會是一成不變的真理。可見,對勞動如何進行消費的研究并不屬于生理學本身的研究對象,它屬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抽象勞動≠生理勞動。也因此,在抽象勞動這個特殊社會發(fā)展規(guī)定性上,人們不應當再提出什么“簡單生理勞動”(所謂體力勞動的抽象勞動)和“復雜生理勞動”(所謂腦力勞動的抽象勞動)來了。“生理學意義上的抽象勞動”當然是不折不扣的對于馬克思抽象勞動規(guī)定的誤讀誤解。
【注:這只是抽象一般的生產關系的勞動范疇上的幻覺。至此可結論說:從抽象勞動奠立經濟形態(tài)社會的生成的規(guī)定上應斷定抽象勞動從一開始就是經濟學意義的抽象勞動,而不會是其他任何種類的勞動。】
這是關注一點,而不慮及其他。耗費的對象只能是也從來是勞動者的生理,所以說這里的作者也像霍奇遜,并不曉得雇傭工人因為失去自我財產保護能力而突顯了“財產的歷史存在性”,而非得把歷史(存在者的邏輯)和假設(存在的邏輯)分開,硬說“勞動力商品概念本身也只能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否則它只會淪為一個僵死的抽象范疇”,目的是從勞動力商品中推導出又一獨立范疇即“勞動力資本化”,作為對“第二大形態(tài)歷史”的一個知識注釋;這亦如西方經濟學的假設,且是不同的條件放松路徑,是歷史條件之辯證放松。這種辯證邏輯知識是假定歷史同樣有理性的狡計,具備施放認識煙幕彈的能力。在這一點上,魯賓已經公正地指出了:“人們不能忘記,在內容和形式關系問題上,馬克思采取的是黑格爾的觀點,而不是康德的觀點。康德把形式當作同內容具有外在關系的某種東西,當作從外部依附于內容的某種東西。從黑格爾的哲學觀點來看,內容本身并不是形式上從外部依附于它的某種東西。相反,通過內容的發(fā)展,內容本身產生出已經潛在于內部中的形式。形式必然從內容本身中生長出來。”【注:博托莫爾:《馬克思主義思想辭典》,陳叔平等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61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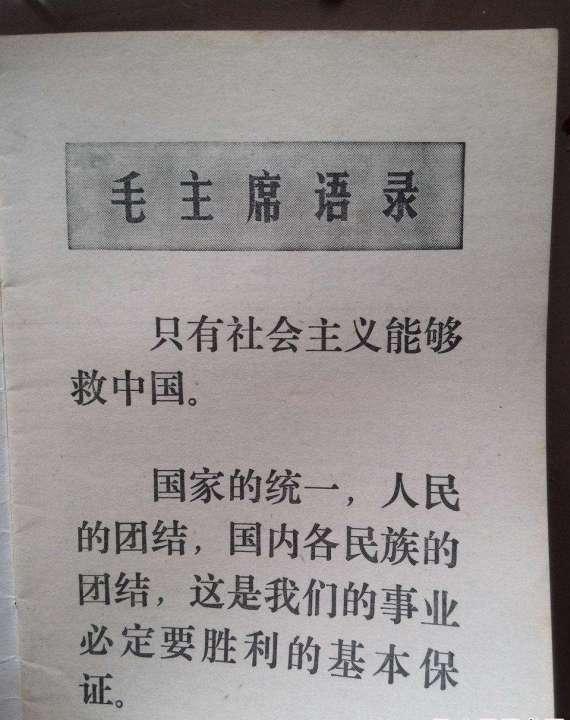
正如身份勞動直接顯示的是“身份關系”一樣,抽象勞動顯示的是價值關系和財產關系,并不由物質關系或物質意義的生理關系代表。并且,這二者指示的均是“勞動之事”,而非“勞動之物”的規(guī)定性。
抽象法工作原像問題
抽象法的工作原像和辯證法的工作原像相對而成,是體用不二的問題。因為一旦辯證法解決了科學領域內的“定義”問題,范疇就不會是純知性的概念,抽象行動就同純邏輯規(guī)定脫鉤。總體而言,這是實踐批判科學的工作啟航。然則,馬克思方法論的革命性內涵終始在于確立總體思維(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力”),其作為歷史規(guī)定的“客觀思維形式”,則在于把握自然、社會、思維過程的統(tǒng)一。
研究方法可據(jù)此確定為學科基礎(“研究內容”)與客觀思維(“研究工具”)之工作路徑意義統(tǒng)一。因此,這里相應所討論的是總體思維形式對具體思維形式的工作領導性問題。各門科學的抽象法,即抽象方法一般,其始源規(guī)定是“范疇的方法”(基于歷史的分析法),而通常所說的“科學的抽象法”,是同時加上了“范疇批判”的規(guī)定。拋開歷史的純抽象的邏輯構圖方法是把科學知識圖型化了,把認識邏輯化了。文本如果僅僅是知識論,——那么意味著:它一旦寫出(從思想母體的產生行程脫開,從中游離出來),旋即被拋棄。然而,這不過是它自己拋棄自己,因為它的封閉構筑體系同時宣判了它的死亡。所以,“‘創(chuàng)造體系’……并不是個別的現(xiàn)象。近來,天體演化學、一般自然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的體系如雨后春筍出現(xiàn)在德國。最不起眼的哲學博士,甚至大學生,動輒就要創(chuàng)造一個完整的‘體系’。正如在現(xiàn)代國家里假定每一個公民對于他所要表決的一切問題都具有判斷能力一樣,正如在經濟學中假定每一個消費者對于他要買來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內行一樣,——現(xiàn)今在科學上據(jù)說也要作這樣的假定。所謂科學自由,就是人們可以撰寫他們所沒有學過的一切,而且這被冒充為唯一的嚴格科學的方法……把一切淹沒在它的高超的胡說的喧嚷聲中。詩歌、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中有這種高超的胡說;講臺和論壇上有這種高超的胡說;到處都有這種高超的胡說……造就出以‘科學’自炫但對這種科學又‘確實什么也沒有學到’的各色人物。這是一種幼稚病,它表明德國大學生開始向社會民主主義轉變,而且是和這一轉變分不開的,可是我們的工人因有非常健康的本性,一定會克服這種幼稚病。”【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4-345頁。】
在此構筑法感召下,于是,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工作型范,經濟學變成一種科學原理,方法論淪為邏輯圖型:它們的工作關系是一種范式對另一種范式、一種原理對另一種原理、一種認識對另一種認識,以致一種科學對另一種科學的無休無止的爭霸與比試。仿佛這就是科學的發(fā)展。這其實是在試圖整體地刪除批判規(guī)定。西方經濟學宣告一切均從科學出發(fā),實則從抽象邏輯出發(fā)。因此,偽科學的普遍做法是使科學工作實際淪落為:表面上抬高科學的位置,實則力圖使人們遺忘科學產生自身規(guī)定的道路。如果把這些內容統(tǒng)統(tǒng)命名為“方法論”,經濟學方法論就只有一條規(guī)范:建造偽科學的體系。那么,實證科學還會剩下什么有價值的東西呢?作為建造體系的法則,它要求一切工作為了體系,除了體系還是體系,除了建筑還是建筑,建構直接替換了工作批判。于是,邏輯化啊,形式化啊,剩下的內容就是盲目地邏輯化和懵懂地形式化;前者多半為了更好“貼近”現(xiàn)實,后者則為了更高水準“解釋”現(xiàn)象。

第四種批判
通過與西方經濟學“假設技術”相調情,在第三種批判中,問題顯得復雜起來。
其一,仿佛政治經濟學不是研究生產關系,而是研究生產發(fā)展的階段性;通過使生產力意義的階段性上升為知識假設,假設本身就成為一切經濟關系的理解標準和邏輯演繹的基點。
其二,勞動力商品成為理論假設的工作技術,是對實體分析規(guī)定的實質性否定,即不關注生產關系本身,僅注重強調經濟范疇=抽象假設的演繹。
其三,而對歷史進行假設,對歷史施以理性分析技術,無異于是把歷史發(fā)展本身看作理性演化的各個階段。生產力的各項技術參數(shù)成為衡量歷史發(fā)展的先進或落后的標準;這種種條件的設置最終顛覆了生產關系的理解標準,作為可有可無的“理性基礎”,使之作為可有可無的“理性基礎”,淪為“本身也只能是一個歷史的概念”。
如下列這種籠統(tǒng)的說法:勞動力資本化——如同“市場經濟”這個術語的產生一樣,乃是知識經濟時代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假設式抽象”工作演繹主義按其內在建構邏輯必然進一步推向極端化,倒向了科學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第四種批判)的懷抱。后一種工作是以在思維領域中炒作“馬恩差異”面目問世的:既然將抽象法的工作原像單純歸結為“科學(思維)規(guī)定”,而不是作為歷史工作規(guī)定的“抽象力”,就認定由于恩格斯太過重視歷史和革命行動,而缺乏了科學的經濟思維,又因之,歷史本身(客觀史和經濟史)不能作為科學構筑元素對待,恩格斯無力把握《資本論》“內在的邏輯”——抽象上升到具體。
【注:參閱羅雄飛教授系列文章《恩格斯與馬克思轉化理論》,載《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3年第1-2、4期;此處的評析多有引申,非限于羅教授本人。】
我們看其中的幾個斷章:
首先,對于馬克思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政治經濟學方法,恩格斯對《資本論》的解讀未能充分加以體現(xiàn)……隨后,恩格斯寫成了“《資本論》第三卷增補”……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所涉及的……邏輯過程是歷史過程的直接的思想反映……可見,在他看來,邏輯過程首先是對歷史過程的概括性抽象,而把典型具體作為特定有機體進行解剖分析,僅僅是“修正”歷史認識的一種補充手段……表明,恩格斯對商品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所作的歷史方面的補充,很難說是合乎馬克思《資本論》的內在邏輯。
這里,斷章先生在內心深處醞釀并想立即講出的其實是這句話:“他沒有真正把握住馬克思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理論特質,沒有把其中的一些具有一般性的約束條件看成是貫徹整個勞動價值論和生產價格理論的約束條件,從而主要依照他所理解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事物的辯證發(fā)展規(guī)律,按歷史的思維解讀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但令人奇怪的是,恩格斯的這種缺點(認識偏差)“對既有的具體結論沒有顯著的影響”,既然沒有什么影響,何勞斷章先生大動腦筋來進行批判,實在是為了“心中的抽象法”——從實證主義邏輯科學方面捍衛(wèi)抽象法。因為那是馬克思的獨家創(chuàng)造,所以“對于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科學性和進一步發(fā)展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鑒于這個真實目的——維護馬克思意義上的科學性,就必須對恩格斯進行工作指正,指出他由于不懂“科學抽象”,“使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定格在批判性理論的地位,難以拓展成為一種能夠指導現(xiàn)實經濟活動的建設性理論。”言下之意,恩格斯使歷史=批判思維,而除掉了科學,撇開了科學思維。但是,這里也要立即指出,所謂“把其中的一些具有一般性的約束條件看成是貫徹整個勞動價值論和生產價格理論的約束條件”:諸如(1)“假定:地產=0”。
【注:討論資本一般時,馬克思要進行這樣的假定——“土地所有制=0”:“只有這樣,才能在研究每一個別關系時不致老是牽涉到一切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8頁)】
(2)“假定工資總是等于它的最低額”,(3)“以勞動剝削程度或剩余價值率相等為前提”,(4)“把各種勞動力直接當作簡單勞動力”,以及(5)“假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guī)律是以純粹的形式展開的”,即“不同生產部門的一切商品都按照它們的實際價值出售”,(6)“政治經濟學必須假定供求是一致的”等等,這些都不過是價值分析環(huán)節(jié)的真實規(guī)定。它們或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極為現(xiàn)實的假定,或是為了突出生產規(guī)定的實體性而設置的運動條件。可以顯見,所謂“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理論特質”,乃是經過斷章先生自我精心策劃的。
其次,馬克思生前與恩格斯關于價值形式的微妙的分歧,對于我們進一步理解馬克思關于商品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馬克思關于價值形式的分析與商品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的分析一樣,都是運用理論抽象力側重于邏輯分析。因此,恩格斯……針對價值形式向馬克思建議:“可以把這里用辯證法獲得的東西,從歷史上稍微詳細地加以證實,就是說,用歷史來對這些東西進行檢驗……就這個問題寫出很好的補充論述,從而用歷史方法向庸人證明貨幣形成的必然性并表明貨幣形成的過程。”……(馬克思)回信說:“至于說到價值形式的闡述,那么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議,又沒有接受你的建議,因為我想在這方面也采取辯證的態(tài)度。這就是說:第一,我寫了一篇附錄,把這個問題盡可能簡單地和盡可能教科書式地加以敘述;第二,根據(jù)你的建議,把每一個闡述上的段落都變成章節(jié)等等,加上特有的小標題。我要在序言中告訴那些‘不懂辯證法的’讀者,要他們跳過……去讀附錄。”從馬克思的回信看,實質上是委婉地拒絕了恩格斯希望補充一些歷史方面內容的修改意見……原因或許是:在他看來,價值規(guī)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特有范疇,價值形式也像價值規(guī)律一樣,僅僅適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此,從物物交換到以貨幣為中介的商品交換的發(fā)展,盡管很容易從歷史上找到例證,且馬克思“在這方面掌握了許多資料”,然而,一旦離開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這些例證提供的僅僅是歷史的形式,并不具有真正的理論意義。例如,“麻布=上衣”這樣一個簡單的等式,如果沒有“商品交換十分廣泛和十分重要”這一前提,生產商品的勞動就不可能真正表現(xiàn)為一種社會必要勞動,這種關系就不可能是一種真正的價值關系……“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而這一細胞只能是“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的細胞。他從中所揭示的價值規(guī)律,也僅僅是“現(xiàn)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guī)律”。
這里,創(chuàng)造一個神話:唯一版本的“獨特的馬克思的思維方法”,是科學思維方法,這是天才者獨有的稟賦。于是,恩格斯最能理解馬克思這個歷史事實被無情摧毀,乃至于要被認識顛覆。這種超人魔方只為馬克思唯一的科學上的繼承人“斷章先生”所獨制。這里,波普爾-馬克思線路上的學院派研究者卻更向我們宣稱:“我不要戰(zhàn)斗,我要的是科學。”似乎是想說歷史思想并非歷史的,而是某個作家依據(jù)非凡思維能力可加以創(chuàng)制的。這兒仿佛是抬高馬克思:馬克思百分百“懂辯證法”,恩格斯則是“不懂的”,于是,“我要科學”,——因為科學意味著容易地將讀者捕獲!可見,委實是言說者自己的心思。
對于這種刻意的言詞上的抬高,馬克思的態(tài)度向來是揶揄加諷刺的,一概加以原封不動地退回。斷章先生以異常的態(tài)度強調:“在馬克思那里,價值規(guī)定只具有最一般的意義,是以諸多假設為條件的最為抽象的本質。”而又莫過于強調:最為抽象的規(guī)定只能在資本主義這個發(fā)達社會中得以實現(xiàn)(“價值規(guī)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存在的”),以致是最后才變出的“真身”。現(xiàn)在,經過包裝的然而是進步了的“波普爾式的馬克思學研究學者”高調推出了英國條件:“作為一種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理論,它對價值規(guī)律的考察是在類似科學實驗室的純粹條件(這種純粹條件是通過抽象力設定的)下進行的。”這又是所謂的“獨特的德國式科學主義”。但德式科學抽象還是忽略了這一點:對生產關系進行內在剖析(這是全部批判工作的基礎),要同時涉及歷史和實踐兩個方面。《保衛(wèi)資本論》第六章舉出《馬克思1880年6月27日致紐文胡斯》中的一些內容,它強調了:歷史發(fā)展內容并不能用經院式的一般詞句來預先予以確定。
【注:也就是在這封信中,馬克思說明:“在目前條件下,《資本論》第二卷(第二冊和第三冊)在德國不可能出版,這一點我很高興,因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經濟現(xiàn)象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

馬克思實際對恩格斯說,“我想在這方面也采取辯證的態(tài)度”——“既接受了你的建議,又沒有接受你的建議”,那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現(xiàn)在的“價值形式的闡述”其實就體現(xiàn)了恩格斯所說的“歷史方法”,——只要在形式(闡述方式)上加以適當調整即可。這也正是附錄經修改移入正文的理由。
再次,恩格斯將馬克思不同理論層面的分析簡單對應于不同社會形態(tài)條件下的商品經濟發(fā)展水平……這種傾向在《<資本論>第三卷增補》一文中表現(xiàn)得最為集中,也最為明確……馬克思不同于恩格斯的地方是,馬克思將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實質與其表達方式相對區(qū)分開來,而恩格斯似乎是將兩者聯(lián)系在一起進行批判。
斷章先生這里想說的是:“恩格斯所說的邏輯研究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歷史研究,是歷史研究成果的一種表述方式。”因其本人是邏輯工作主義導向,就武斷認為:“馬克思關于價值形式的分析與商品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的分析一樣,都是運用理論抽象力側重于邏輯分析”,所以關心的只是如何將黑格爾的“虛假的實證主義”變成馬克思意義上的“真實的(即科學的)實證主義”。
【注:這和斷章先生作為一名極為稱職的經濟學領域內的史學工作者的榮譽稱呼是相違背的。他應該深知對馬克思思想的研究分為“傳”“評”“論”越發(fā)深入的層級,是傳主的思想認識通達研究者本人和讀者的過程。但是,這位先生不幸顛倒了這個過程的起始環(huán)節(jié),過多地以“論”居主,反弄成“挾天子以令諸侯”。本來從紀傳的要求上看,適當強調馬恩差異,乃能達到烘托傳主的藝術構境效果,這種多層次的差別記述無疑屬上乘史筆。但是,如果從“論”入手,用哲學詞句預設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內容和思想形成過程,并對創(chuàng)始人予以分立和對置——如對馬克思用科學的實證主義概述、對恩格斯則用物性論的黑格爾主義概述,則明顯地是忽略了創(chuàng)始人所共有的歷史創(chuàng)造場境,且無視他們作為工作互補含義上的對當時歷史的成功代言這一基本事實。這當然是對史過程本身的割裂,犯了嚴重的邏輯工作主義錯誤。盡管斷章先生們對原始意蘊的“馬克思科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史海鉤沉,但很難說他弄懂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工作關系,而兀自不承認二者的有機統(tǒng)一,時而就在它們中間搞分裂或對立。】
而恩格斯沒有朝其預想的這一方向去進行研究。所以在實證主義方面,他要說馬克思是黑格爾主義的,在反對唯心主義方面,卻要反過來說:“恩格斯……所突出的,是獨立存在的事物的自為的辯證發(fā)展,因而具有濃厚的物性論色彩,一定意義上可以看成物性論的黑格爾主義。就此而言,把恩格斯的哲學稱為‘歷史唯物主義’更為準確,何況,他本人沒有使用過‘辯證唯物主義’這一提法。”
最后,對于黑格爾哲學的體系所具有的形式,恩格斯盡管強調要“批判”地消滅,但他并沒有給我們發(fā)掘出這一“形式”所具有的積極意義。事實上,黑格爾哲學的體系,作為其思維形式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甚至被簡單地拋棄了……馬克思也深知,恩格斯不擅長他所運用的科學抽象法……這種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科學抽象法”,體現(xiàn)了德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與近代科學精神的結合。它一方面保持了德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的從本質到現(xiàn)象、從抽象到具體、從整體到部分的基本特征,同時又使理論的邏輯展開與知識的發(fā)現(xiàn)、發(fā)展和廣泛運用的“科學進程”相結合,從而克服了它的神秘主義色彩。古典經濟學限于抽象分析的弊病也因此被克服。
博愛論者以為自己是在嚴肅反對資產者的實踐,其實,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它。為了襯托馬克思的“科學抽象”,馬克思前面的先驅者——古典學派也被硬說成“限于抽象分析”,但是馬克思恰恰說他們“抽象還不夠充分”,“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虛假的。”所以,必須鄭重指出:斷章先生余下的指責,均是出于對馬克思不理解而引發(fā),卻誣為恩格斯對馬克思的“不理解”。
【注:相比馬克思,恩格斯不懂什么呢?科學的邏輯實證的人本主義思維與方法也。蓋言“科學實證主義”,乃是指:《資本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作“活的生命體”,把商品當作它的“細胞”,把經濟研究視作一項“生理解剖”。然而這種思維與方法本質上與經濟史的事實是無涉的,仿佛所有的變化均在“活的生命體”內部進行,或是從一個活體轉向另一個活體。其對知識論邏輯之推崇,可用這一段話總結之:“它要求科學認識進程始終圍繞特定的客觀對象,要求嚴格地排除脫離特定的客觀對象的抽象的演繹推論。‘概念即對象’是它的一項基本原則……(于是)辯證法與實證研究的結合,既需要通過從具體到抽象的實證研究把握特定的客觀對象的內在本質規(guī)定和一般原理,還要更多地要求從已經掌握的本質規(guī)定和一般原理出發(fā),用實驗科學的方式,將一般的或本質的規(guī)定具體化為對特定客觀對象(而言)的系統(tǒng)的、整體的、有機的知識體系。這就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完整含義。”(羅雄飛:《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思想——以科學實證主義為核心》,經濟日報出版社,2017,摘要,1-2頁)】
例如說,“馬克思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分析方法以實踐唯物主義為基礎,將黑格爾式的思維形式與近代科學精神結合起來,由此形成的理論結構類似于一種先驗的結構。”據(jù)此可見,“恩格斯的‘現(xiàn)代唯物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傳統(tǒng)唯物主義的束縛,具有‘物性論’色彩;它與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相比,在理論高度上存在相當?shù)木嚯x……把黑格爾的思維形式與‘絕對精神’一起拋棄掉了。”還有諸如此類的說法:“用一種歷史的思維來解讀價值規(guī)律……用歷史發(fā)展的思路解讀《資本論》……由于恩格斯不承認馬克思經濟理論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體系,并把生產價格與現(xiàn)實經濟中的市場價格混為一談,這就難免引起一些邏輯上的混亂。”不一而足,無不顯示了對于“抽象”的歷史知識的無知。
科學解剖主義除了和科學結構主義具有類似的工作性質:把對象看作死的對象(即便把對象換成研究對象亦是如此),還轉而把文本看作死的文本。關于這一點,前面講的已足夠多了,這里不再贅述。只重點提出一點辯駁:究竟誰是物性論者?斷章先生在這里對“麻布=上衣”的邏輯表現(xiàn)出理解上的極大的障礙。
【注:其用“物性論”這個術語表達以下意思:恩格斯對唯物主義的過度重視,以至于用物性統(tǒng)率人性,用唯物主義統(tǒng)率人本主義,用經驗實證的歷史辯證研究統(tǒng)率科學辯證法,概言之,指責恩格斯的“現(xiàn)代唯物主義”實質上是基于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一種物性論思想。其實,這是對恩格斯學說的典型的斷章取義。真正把物性看作人類社會和一切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本性,看作必然性認識的是資產階級理論工作者,并非恩格斯。物性論意圖——它的真正意旨——在于用物質性、物象性掩蓋認識上的辯證法,遮掩歷史主義規(guī)定,極力以“強制性結構”屏蔽掉一切用于批判的有價值的元素。】
或者有意地誤會,或是刻意地裝作漠視,卻大言不慚說“馬克思把理論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馬克思的回信對這種“故意”現(xiàn)象予以了充分揭露:
經濟學家先生們一向都忽視了這樣一件極其簡單的事實:20嗎麻布=1件上衣這一形式,只是:20嗎麻布=2英鎊這一形式的未經發(fā)展的基礎,所以,最簡單的商品形式……包含著貨幣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將包含著萌芽狀態(tài)中的勞動產品的一切資產階級形式的全部秘密。在第一次的論述(《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只是當價值表現(xiàn)已經以發(fā)展的形式即作為貨幣表現(xiàn)出現(xiàn)時,我才對價值表現(xiàn)作應有的分析,從而避免了闡述中的困難。
又恰恰是在這封回信中,馬克思對恩格斯說:
此外,你從我描述手工業(yè)師傅變成——由于單純的量變……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證了黑格爾所發(fā)現(xiàn)的單純量變轉為質變的規(guī)律,并把它看作在歷史上和自然科學上都是同樣有效的規(guī)律。【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215-216頁。】
解決了“如何來”,才可能進一步解決“如何去”。而揭示生的過程恰恰是為了預示死。在此意義上,量變到質變的原則就莫過于實現(xiàn)對象的“生死實錄”。只有用嚴重帶有預設色彩的資產階級物性論的觀點看問題,才會死抓住資本的知識定義不放:既不愿向前看,也不愿向后看;仿佛就是新康德主義者:因為死抓住可認知的“定義”,而絲毫看不到以商品為基礎的價值學說對以貨幣為基礎的價值學說的質性結構上的轉換性,以及相應的對以資本為基礎的價值學說的工作轉換性。所以關于“價值形式的闡述”的理論特殊性質,馬克思事實上是如此強調的:
(1)蒲魯東主義被連根鏟除了,(2)通過最簡單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闡明了資產階級生產的特殊社會的,而絕不是絕對的性質。【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149頁。】
君在長江頭,我在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與君同飲長江水。這是批判四要提交給讀者的見解。此是顛倒也。翻譯一下就是:馬克思經濟學是抽象的源頭——對這一點西方經濟學是視而不見的,它們本身則是“抽象現(xiàn)象論”,如欲再飲長江水,勢必要在長江尾,而這就是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共同宏旨,也是交集。此新綜合之論。

![]()
————————————————
![]()
持上述觀點的人乃是以綜合語境中的經濟學作為構筑論說的歸宿。由于平素懷有綜合之心,所以一般人當其被問及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方法時,總采用兩種作答方式:(1)歷史方法類型;(2)邏輯方法類型。中間有一些閃爍其詞者,那是因為要兼顧這兩種類型。因為同時遵從歷史和邏輯,就會覺得為了達成兩者一致的原則,邏輯的方法優(yōu)于歷史的方法應是工作前提,因其更能表現(xiàn)歷史,歷史的方法不大能實現(xiàn)對歷史自身的有效表現(xiàn)。這是將內容和形式的關系“邏輯化”“游戲化”了。于是造成歷史方法的“非經濟學科化”以及邏輯方法的“文本語義化”,而這一切的結果導致了邏輯優(yōu)先的“經濟定義”產生。然而,其不能否定歷史方法從來是內容、邏輯方法從來是形式這一規(guī)定。相對歷史的本體邏輯,范疇生產從而工作批判的方法,不過就是科學方法本身。
而我們之所以強調研究方法即政治經濟學批判意義的發(fā)生學,學科方法同時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或邏輯方法,為了申明方法實體結構的重要性,乃著重強調歷史范疇生產對范疇批判工作轉換的重要性。并且在這里,也要強調作為總體思維和客觀形式的“抽象力”(如中國學科與方法的“天人合一”“陰陽”以及馬克思所說的“二重性規(guī)定”)和作為一般思維活動(規(guī)定)的“抽象思維形式”的區(qū)別。而這樣一來,也就有了抽象法的二次表現(xiàn)過程:這不是單純的體系構筑,主旨在于明確實踐化的批判規(guī)定,不單純是生產“范疇”,從批判角度看,目的也在于生產“邏輯”。批判規(guī)定的學科方法必須具象化,以尋求適當?shù)墓ぷ餍问健?梢姡唧w的科學方法——結構的方法或者數(shù)學邏輯方法——不過是學科方法實體的進一步工作變形,是因循具體對象分析特性的形式化的結果,是對歷史方法賦以“血肉”。
整個工作轉換是程式化與非程式化的統(tǒng)一,依據(jù)對象和問題性質不同,具體而論。例如在思想史領域,作為認識(批判)方法,從抽象規(guī)定或范疇出發(fā),以固定好路線的方式——如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進行,往往能夠收到極好效果,因為這是人體解剖,是黃昏時刻起飛的貓頭鷹。就認識的這種工作性質而論,其往往會成為理論批判和建構的先導,宜采用程式化的方法或形式。但對客觀邏輯的批判行程來說,則不應有固定程式,實際是依據(jù)質樸的發(fā)生學來予以安排,工作邏輯往往由實際的材料(發(fā)展過程和生活過程)所支架而成。這里沒有藥方或公式。如馬克思對價值形式和生產價格形式的考察,只涉及對發(fā)展行程的具體運動方面的考察,其實當中并無多少抽象元素。《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實際上并沒有全部完成對于生產價格形式的考察,只是勾勒出這種歷史考察的大綱,就是:(1)從市場價值和生產價格的歷史轉換關系中尋找它的最初的形式;(2)從資本有機構成在產業(yè)資本內部的變動不居,繼而產業(yè)資本和商業(yè)資本相互關系中尋找發(fā)展的形式,亦即其總和了的擴大形式;(3)復又從資本分配具體形態(tài)生成運動把握其一般形式,這是一般利潤率的社會實現(xiàn)關系;(4)而從資本總體精神現(xiàn)象學中把握的批判形態(tài),乃是它的成熟化了的形式、它的進一步變異了的形式,即虛擬形式。最后一者是一般形式的特殊轉化工作形態(tài)。但是,全部工作至此并不算是得到了妥善的解決,因為“全部臟東西的分解”在運動中完成,“結論就是階級斗爭”,斗爭形式是伴隨運動的界限的規(guī)定進行的,這就是一般利潤率下降規(guī)律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運動。在這當中,得以貫徹到底的中心線索是一般利潤率的社會生活領域的表現(xiàn)。實質的關系一般利潤率對平均利潤率的形成運動,產生了以平均利潤率(表現(xiàn))為運軸的全社會的利潤一般分割關系。
現(xiàn)將問題稍稍匯總一下,以力求給出具有明確性內容的分析說明。事實上,整個理論(認識)生產歸屬歷史支架的發(fā)揮作用的過程,中間亦有認識支架發(fā)揮作用的因素,二者有時又同時在場,有著特殊的工作統(tǒng)一性。這方法論=邏輯,而又排掉知識論=邏輯的工作場合,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歷史支架可限定為由“歷史”支架的理論建構規(guī)定,認識支架可對應限定為“認識”直接支架的理論規(guī)定。
而要再提《1858年2月22日致拉薩爾》。【注:《保衛(wèi)資本論》最初在第三章,又在寫認識發(fā)生學原理的第十六章提及了它。】
馬克思在當中最初安排了三部著作:(1)《六分冊計劃》;(2)《社會主義批判》;(3)《對經濟范疇或經濟關系的發(fā)展的簡短歷史概述》。馬克思打算將前兩者合并在《對經濟學范疇的批判》中,這樣整體來寫:“資產階級經濟學體系的批判……是對上述體系的敘述和在敘述過程中對它進行的批判”,敘述方式“是完全科學的”,因而一點也不違犯警章。這其實說的就是范疇生產,即歷史支架的安排理論的情形,所以馬克思要強調說:“當然,我有時不能不對其他經濟學家進行批判,特別是不能不反駁李嘉圖,因為作為資產者,李嘉圖本人也不能不犯即使從嚴格的經濟學觀點看來的錯誤。但是,總的來說,關于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批判及歷史應當是另一部著作的對象。”眾所周知,第二部作品馬克思并沒有實際地寫出來。并且也就是這里,馬克思說明了最初決定以六分冊的工作計劃形式出版自己作品的一個重要理由:“進展很慢,因為多年來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些題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們,總是又出現(xiàn)新的方面的問題,引起新的考慮。加之,我并不是我的時間的主人,而寧可說是它的仆人。給我自己留下的僅僅是夜里的時間,而肝病的經常侵襲和復發(fā),又使這種夜間工作受到妨礙。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我能把全部著作不定期地分冊出版,那對我來說是最合適的了。”【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9-150頁。】
這也使我們聯(lián)系起“理論的先驗結構”,其實是對于《六分冊計劃》并入《資本論》四冊結構的一種講法,因為后者相比前者更加清晰地執(zhí)行了上述任務。
【六冊計劃注:實際執(zhí)行中,分冊的數(shù)量毫無疑問地會明顯增多,——這是不可免除的,也是馬克思當時較為“煩惱”的事情。比較一下“分冊出版”和后來馬克思一再提起的“藝術的整體”,人們或許能夠明白:馬克思后來選擇將整個著作同時完成,委實包含了對于方法論的深思,這就是研究和辯證講述的統(tǒng)一。】
【四冊結構注:馬克思擬訂的是“三卷本”的結構形式。之所以如此,還是想要藝術地執(zhí)行“三部著作”計劃,所以也一再地提及社會主義批判問題。在這里,馬克思把完整的敘述同時看成“方法論”,這是特殊的邏輯科學,指導人們如何生產知識,如何進行工作批判。一句話,研究=歷史(=工作邏輯,即方法的本體形式),敘述=方法論(=邏輯,即工作邏輯的形式),從而研究的過程涵容在辯證的講述中了。】
馬克思在《1858年11月22日致拉薩爾》中交代:“材料我已經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給它一個形式。然而,在我所寫的一切東西中,我從文體上感覺出了肝病的影響。而我有雙重理由不允許這部著作由于醫(yī)療上的原因而受到損害。”他總要強調:“我所追求的不是優(yōu)美的敘述,而只是寫出我平素的風格。”【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67頁。】
關于安排理論的歷史支架和相關認識工作支架結合的場合,馬克思還這樣說過:“我還是打算把地租理論放在這一卷作為增補,即作為對前面提出的原理的‘例解’。”這是馬克思在《1862年8月2日致恩格斯》中說的話。“這一卷”指《資本論》第一卷最初方案,眾所周知,地租后來放在了理論結束部分闡述了。之所以要像前面那樣考慮,是因為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問題進行考察需要;按照客觀批判的要求,所謂六冊工作計劃,原初意旨就在于對這個生產方式的基本條件進行逐一批判;之所以采用后面的方案,是因為按照認識支架,資本主義地租理論之被提出發(fā)生于下屬場合:(1)“李嘉圖把價值同費用價格混為一談。所以他認為,如果存在絕對地租(即與各類土地的肥力無關的地租),那么,農產品等等的出售價格就會由于高于費用價格(預付資本+平均利潤)而經常高于價值。這就會推翻基本規(guī)律。所以,他否認絕對地租,只承認級差地租。”(2)“關于和價值不同的費用價格的上述規(guī)定,還應當指出,除了從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產生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qū)別,還有從資本的流通過程產生的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區(qū)別。”所以可以看到,“對李嘉圖的理論的批判……由于考慮到了資本的有機構成,許多一向似乎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都消失了。”(3)“如果上述觀點是正確的,那么,根本不必在一切情況下或者對任何一種土地都支付絕對地租……凡是土地私有權(事實上或法律上)不存在的地方,就不支付絕對地租。在這種情況下,在農業(yè)中使用資本就不會遇到特殊的阻礙。資本在這個領域中就會像在其他領域中一樣毫無拘束地運動。于是農產品就會像許多工業(yè)品那里常見的那樣按低于自己價值的費用價格出售。在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是同一個人的場合,土地私有權實際上也會失去意義,等等。”(4)“土地私有權的確(在某種歷史情況下)提高了原料的價格。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來看這是很可以利用的。”【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5-190頁。】
產品社會的發(fā)展支架在這里起“認識干擾”作用,宜并入認識支架考察。它作為分配因素而起作用。看來,認識支架在很多方面的確給歷史支架的生產(客觀批判)提供認識導航的作用,無論主客體的批判體系,均是如此。一般而言,歷史支架構成社會生產方式運動的骨骼,如勞動一般的運動、資本一般的運動,這是廣闊的歷史發(fā)展視野;與之同步,認識支架也規(guī)劃著運動骨骼中的具體內容,如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結合,以至于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結合等等,這是社會運動內容的實際表現(xiàn)和細節(jié)方面。據(jù)此而論,一方面支架必然是結合一體的,另一方面也同樣需要把認識支架獨立出來,以更有效組織認識生產和進行批判。整體上看,學科方法可以視為確定性程式與非確定性程式的統(tǒng)一。顯然,與歷史支架內容有關的屬于后一方面的分析,代表實踐化工作的取向,而與認識支架內容有關的,乃是屬于前一方面,它部分滿足了對認識予以形式組裝的分析與綜合的兩方面的理論渴求。

【附注:實證小資料】何謂實證?所謂“經驗的事實”,就是實證的對象和實證的內容;所謂“歸結為”,就是探索或者追溯;所謂“歸結為某種經驗的事實”,就是進行實證的過程,以及由此顯現(xiàn)出來的實證性。而從詞義上講,所謂實證,就是“實際的證明”。英文“實證”(positive)一詞,來源于拉丁文Positivus,其原意是“肯定”、“明確”、“確切”。在法國哲學家、實證主義創(chuàng)始人孔德看來,“實證”一詞具有真實、有用、精確等含義。據(jù)考證,馬克思早在 1841 年的《博士論文》中,就已經使用了“實證”以及“實證哲學”的概念。在著名的唯物史觀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了“實證科學”的概念。不論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不論是實在論者還是非實在論者,不論是堅信客觀實在還是否認客觀實在,若是在科學的語境中進行思考,那就必須將實證檢驗作為理論比較的試金石,而不能僅以抽象邏輯作為判斷科學與否的唯一依據(jù)。在方法論的語境里,實證的含義一言以蔽之,就是任何論點都必須從事實出發(fā),都必須給出經驗證據(jù)。實證的目的和實證的結果有兩種可能:其一,證實,即“證明其是事實”,或“證明其是”;其二,證偽,即“證明其不是事實”,或“證明其否”。令人感到荒唐的是,放眼望去,“只限于描述事實”之流的“無與倫比”的做法,如今依然是“現(xiàn)代經濟學”追求的最高目標。實證的基本任務,只在于回答“是什么”(what)和“為什么”(why)。把實證分析等同于定量分析,則是對實證分析的嚴重誤讀。又之,不論是定量實證還是定性實證,在不同的方法論指導下,實證的結論將大相徑庭。因為實證既是感性的,也是“非中性”的。并且,不僅經濟學的實證分析不可能是中性的,即使是自然科學的實證分析也是“非中性”的。須知方法論的認識過程,是“實踐的觀點”;用計量經濟模型“跑數(shù)據(jù)”,雖然能夠實證出經濟變量之間的真實關聯(lián),但是,這種關聯(lián)背后的內在根源仍然有待于經濟理論的進一步揭示。馬克思揭示資本主義發(fā)生、發(fā)展內在規(guī)律的《資本論》,是不能依靠計量經濟學的“跑數(shù)據(jù)”來完成的。亦是說,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依靠“抽象力”,依靠辯證的“抽象力”。庸俗經濟學家之所以“緊緊抓住了外表”而“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lián)系”,其方法論的根源就在于他們的“抽象力”不是“辯證的抽象力”,而是“形而上學的抽象力”。計量經濟學之極力回避經濟變量間的矛盾關系,其方法論的原因就在于,計量經濟學遵循的邏輯是數(shù)理邏輯和形式邏輯;蓋因缺乏辯證的“抽象力”,不懂得運用矛盾分析去正視和處理“內生性”問題,當其面對經濟變量之間復雜的矛盾關系,計量經濟學只好避之唯恐不及了。也就是說,盡管西方經濟學始終強調把自然科學中的實證工具引入經濟學的研究之中,但是,由于不能運用唯物辯證的“抽象力”進行分析,結果在歷史觀上無法擺脫唯心主義的束縛,因而使得自然科學中的唯物主義邏輯始終不能貫徹到經濟學領域。所以歸根結底,實證的性質在于方法論的性質,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證性質,奠定了堅實的方法論基礎。唯物辯證的“抽象力”則是政治經濟學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實證性質的具體路徑。(選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何以“實證”》)

主體內容轉自《保衛(wèi)資本論》修訂版P559-610
許略,編輯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

